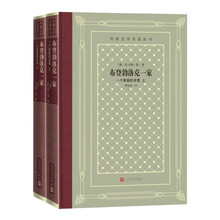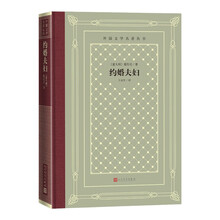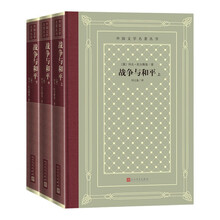第一辑 端一轮月亮照见我
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
1.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我叫李蕾。
在这个世界上,五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是阔叶乔木浓密的树冠,我就住在树木的头顶上,可我常常以为这里是深深的海底,我永远记得,“在大海的深处,海水像矢车菊那么蓝,像最亮的玻璃那么清……”
在这样的海底,只有我一个人,从卧室到达客厅需要六步,其间穿过一片玻璃般透明的蜘蛛网,它们是我的海底森林。
2.我不停地想要改变。
我买了很多衣服,衣服让我看上去像完全不同的人,当我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或者索性什么也不穿,我惊奇地发现,从卧室到客厅依然需要六步,生活并没有因为衣服发生任何变化,我依然孤独。
眼睛走出去,外面是花园,有彩色的滑梯和秋千,种着《大西洋底来的人》里那种神奇的蔷薇,还有日本樱花,大叶女贞和竹子。只要我跟着眼睛走出去,所有的孤独就会从树顶飞向高高的天空,像野鸽子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我把自己关起来,一遍一遍洗澡,沐浴液发出海洋和松树的气息,我保存煮过的咖啡粉末,它能让鼻子保持灵敏,我嗅嗅它,再嗅嗅自己,害怕一个人呆得太久太无趣,会变成僵尸,像中世纪的古堡,里面住着因为复仇而永生的灵魂,拖曳着华丽的绸缎长袍,血管里被填满防腐香料。
孤独包裹着我,有色泽有纹理,一层坚硬洁白的孤独。连偶尔飞过的鸟也知道,包裹生命的蛋壳异常完美,但它并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必须啄破它,挣裂它,才能在天幕中展开斑斓的飞翔。在梵文中,鸟被称为二次诞生,先民们还认为蛇长生不死,它每一次蜕皮都能重生,还有水,水也是永恒的,它可以自己饮下自己。那么我呢?一个人怎样才能挣脱孤独的命运?当我写下这些字,它们就来治我的病,像一片密密麻麻的针眼儿,扎进我滚烫的屁股里,又痛又怕,获得拯救。
3.我准备开始写了。
有必要提醒你,这是一句充满了误解的话。
一切都不是从准备开始的,谁能为了吃饭准备一个饥饿的肚子?为解渴而准备舌头?写字就是自然降临的。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它不请自来,如同少女的初潮,伴随着紧张和疼痛,赋予一个身体某种能力。
我想再提醒你一次,这种能力虽然无法培养,但它并不是与自我分离的,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上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七个女生一起看《红楼梦》,一起练字,在课本的边角上抄唐诗宋词,记住大量诗人的名字,这也许是七十年代生人鲜明的青春,人人都是文学青年。我们学习贾探春组织了文学社,各自起笔名,互相鼓励,说总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个会写得比三毛、张爱玲更好。
七个人里最会笑的那个女孩子,笔名叫绿姑娘,因为她刚刚看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维特第一次见到夏绿蒂,她正把一块蛋糕分给孩子们,穿着一条绿色的裙子。那时候,“维特”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本书,在传阅的过程中,书角翻卷,封面溅上了几粒小小的酱油。
大约十年过后,我又见到绿姑娘,她当了女工人,准备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精算师,她说全中国只有20多个精算师,儿子吃了这碗饭就不用再担忧了。我在她面前闭上嘴,闭合嗓音里荡气回肠的青春,十年前,她没有发表过任何一个字,她是我的绿姑娘,现在一切都变了。
变化的力量从意想不到的角度联合在一起,越来越像一种运动。我知道每个人都曾经有过坐下来写东西的想法,只是有些人无法忍受孤独,他们找到了逃避的方法,另一些人忍耐下来,成为作家,这并不神秘。
4.我不喜欢见人,他人是无底的黑洞。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正在一步步走向约会的反面,我越来越喜欢一个人呆着,关上门,很少饥饿,甚至不再需要什么,房间里到处都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孤独,谁也拿不走,空中飘浮着难以描述的气味儿,像钢铁厂在制造一艘大船,或者是一头獾正在被炼成獾油……早在很久以前,人们已经发明了在封闭的容器里蒸馏鲜花,得到一粒粒迷人的水珠,现在我蒸馏着自己,我开出的花儿太骄傲了,因此耗尽了理智。
我在闷热的回忆里辨别出2002年的气味儿,那年四月,我跟着车队在青藏公路上走了十多天,翻越唐古拉山口,在拉萨街头跟踪磕长头的女人,八角街上威风凛凛的康巴汉子给我看了他的腰刀。第三天,我租了当地的吉普车去看天葬,司机是藏族人,他告诉我,在太阳升起的那座山上住着隐士,隐士们盘着腿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更高的树上。天葬开始之前,喇嘛先要点燃一种植物,叫做信香,烧出白火苗,一股白烟笔直地朝上走,像一把斧头直立在半空,又朴素又纤细,将山一劈两半。接下来,秃鹫来了,如同黑黢黢的森林千军万马的倾塌下来,翅膀铺天盖地,辉映着轰隆隆的风。那种风让我忽然流出了泪水,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哭,似乎这颗心生存到了必须要哭泣的地步。
在五层楼的高处,我再一次泪流满面,孤独就是我的信香,当它燃烧起来,成千上万的文字会在空气中呼啸而来,文字就是食人的秃鹫,用锋利的牙齿啃噬我,用咒语驱使我,吃光了我的身体,逼迫我的魂魄写出第一个字,一旦它被写下来,就具有独立的命运和未来,不归我,也不被任何人决定。
实际上,在我开始写之前,它已经在那儿等候着。
5.把窗户弄暗,打开台灯,坐下写。
绝对不要在背后看,那些字的形成不允许观看,它们羞涩,羞涩到你难以置信的地步,相信我,目光能让它们大面积死亡。在这个角落里,没有眼睛,只有我单枪匹马的一颗心在跳,我在心里说,宝贝,你们来吧,往下跳,每一个字都踩踏着活蹦乱跳的心。
我的台灯像一个驼子,鼻尖上驮着一枚灯泡,安放在房间的死角,我的每一字都是这个死角生出来的。有人问我怎样才能不停地往下写,我不知道,我从来没那么强悍,很多时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等待,发呆,眼看着大块大块黑色把房间填满。
即便是空白的也不需要被打扰。独自在家的下午,我听到这栋楼里有人唱陕北民歌:兰花花开完红花花开,黑夜里想你没办法……歌声让我难过,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肯定有和我一样感到难过的人,我们仰望的是同一个星空。
还有一次,楼下有人吹了一夜萨克斯,他扎着一把又黑又直的长头发,走路一蹦一蹦的,背影像一匹马,我在阳台上看见他,就蘸着水在花盆上写一个马字,花盆里种着杜鹃,繁盛季节一天开一百朵花,第二天,所有的花都枯萎了,我知道杜鹃花跟着马走了,如果你见过一匹白马,腿上重重叠叠摞满花纹,就是我家的杜鹃花附在那里的。
6.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夏天的空气里有爱情,花草都长疯了,我写得很慢很少,心里乱。
后来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工人在楼下修剪灌木,拿着一把大剪刀,我很想知道剪下来的叶子最终会被运到什么地方,万事万物都要面临最终,有一天我也会死去,我希望找到一个人,把我的骨灰喝下去,用一个活的身体,而不是冰凉的盒子来葬我。
7.什么时候我学会写第一个字?那些字教给我什么呢?
似乎再也找不到答案了。我当小孩子的那些年,太阳似乎比现在白,雨点比现在大,人也更勇敢,不怕感冒、不怕陌生人、不怕弃丢家门钥匙。
我曾经喜欢过淋雨,下雨了我不跑,跑了前面也在下雨啊,就有那么一次,我在雨地里走,头发和衣服竟然没湿,很神奇,我走在了雨的夹缝里,一直走了这么多年:现实与梦想,喧嚣与孤独,底层与珍珠,爱与恨……一道道夹缝,犹如一道道光芒四射的闪电划过,在我身上留下明亮的擦痕。有时候,我故意把伤痕夸大,是要哗众取宠,博得某些爱意,但是我从来不后悔,也不曾侮辱那些字提供给我的生活。
看过一个中国故事,画家要画一只老虎,为此穷尽一生,最后,那只老虎从画布上下来,吃掉了画家。我就是那个写字的女人,我叫李蕾,有一天,现实中的李蕾也会被她所创造的那些字吃掉,以身伺虎,立地成佛。
百合心
我知道你一直在看我写的这些字。
我并不想见到你,写的人和读的人,永不相见才是成全。
钱钟书有一部未竞的长篇小说《百合心》,他说,人的心就像百合一样,一瓣一瓣地剥落,到最后一无所有。
我喜欢这三个字,百合心。脆弱清凉的心,我一直认为自己能写的就是寂静的个人体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道路和内心,一些微小但郑重的碎片。
有人问我,你写的那些都是事实么?我只能说,那些内心都是真实的。我把一句话写出来,这句话就不再属于我,有时候我惊奇的发现,它们自行创造生命和意义,这是很好玩的事情,它们从我的心灵里长出来,让我扩大了。
我不能对自己写出来的任何东西做出任何判断,我只想不停地往下写,写那些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和复杂意象的句子,并期望它们善良、干净、有光芒。
有时候我看到自己的未来,那些字像水一样流动、易变,最终消失,它们带着我的个人气质,面临误解和放逐,我只是不停地写啊写,直到这颗心像百合一样落尽,一无所有。
秘密
我喜爱数字的7,它是我隐秘的生命密码,意味着历经曲折总要相见的人,无数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错,对善变的忠心耿耿,对气息和颜色充满警惕。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喜爱,说明我并不了解住在我身体里的这个灵魂,很多时候我们对峙,窥视,相互折磨,只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认为,生命存在就是为了说莫名其妙的话,做莫名其妙的事,莫名其妙的流泪和快乐。
如果每一天每件事都是有用的,会让我无法忍受。
我只关心美的东西,不管它是否实用,我看不见眼前发生的事情,却对遥远的神话时代异常了解。我知道嫦娥为永生痛苦,蛇妖是女娲从公鸡蛋里孵化出来的,与黄帝大战的年代,蚩尤族的女子生了十个儿子,他们住在东海,每天早晨去盐池洗澡,盐池旁边长着一棵扶桑树,粗壮茂密,一直长进云霄。
这些是挂在我神经上的秘密。
普通人等待生命向自己展开秘密,少数人,他们是被挑选出来的,他们本身就是秘密,是生命的雕塑、油画、音乐、是独立的艺术品,不受天地指挥。他们是美丽的人生,美丽的脸和美丽的灵魂,他们引起我的疼痛,如同一个故事,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并不怎么重要,但主人公的悲欢却能悸动人心,让敏感者复活,让麻木者受伤。
我不是个聪明的人,也不够了解自己,被别人赞美聪明我还要生闷气,我讨厌聪明,它有一种强大的破坏力,破坏了美的和谐。我不够美,也畏惧美,它太容易消逝,像一种随时都会被夺去的特权,令拥有者惴惴不安。才华也许比美持久一些,因此我从小就被告诫应该学这个学那个,学所有被认可为才华的本领,一旦遇到真正决定命运的关头,即便有惊人的才华白送给我,我依然糊涂,犯那些已经犯过的错,并且执迷不悟。
年纪越长,就越发觉生命是一个秘密,后天学来的技巧和知识都不可靠,假如没有被命运挑选,百般不及他人,我也宽容了自己,谜底不过如此。
想做的和不想做的
我想做的事:私奔,写让自己满意的东西,泡功夫茶,看完书架上的书,睡懒觉。
我不想做的事:上班,早起,运动,见人,看完书架上的书,写让自己满意的东西。
我把它们写出来,长久地看着,这是两个不同的我,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厮打一团难分彼此,我不理解它们为什么不能一刀两断,可是我的不理解并不表示它们会消失不见,在没有好办法之前,我允许它们吵架,尽量吵得短一些,允许它们悲观,但一定要在活着的时候与命运和解,允许它们制造危机,但要有谈笑间灰飞烟灭的气度。
有一次去大学讲座,我说自己是很分裂的。有个女学生问我,为什么要分裂呢?她的眼神很清澈。我不能撒谎,可我真的不知道,很多事情都没有因为所以,只有结果,这个结果一下子出现了,它刻不容缓坚不可摧,我们才试图在回顾中寻找蛛丝马迹来证明它。
有意思的是,种种矛盾纠葛对于写字的人来说都是恩赐,我只是一个又一个结果相加的总和,文字才是此间千折百回的漫长回顾,想得好却做不到,对我来说是常有的事,此间的赴汤蹈火、手刃强敌皆可成为纸上的惊心动魄。
茅山术与狐狸精
杨锦麟是我的朋友,他和茅山道人是好朋友。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秘密,说出来是不是泄露天机,书上说茅山道人法术厉害,他们在村口的大树下挖一个坑,把衣服埋在里面,整个人就消失了,科学的说法是“隐身”。这个隐身人大摇大摆走进村子,没有人看见,他在农家玩,玩累了呼呼大睡,饿了就去人家厨房吃东西,他没钱,所以师傅规定:吃了人家的东西一定要在灶台上拉一泡屎,类似于梁山好汉在墙上题字:杀人者××也。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不遵守这个规矩,法术就被破了,以后再不能隐身。
杨锦麟问过茅山大师,说我今年走鼻子运。
我有点懵,完全不了解我的鼻子,通常是这样,最不易了解的就是我们最为习惯的东西。
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星球,心脏的“脏”和肮脏的“脏”是同一个字,六一是成年人最想过的节日,电台主持人问一个小孩子最想要什么礼物?他说,弟弟。某些人因为扮演穷人而变富了,我头朝上走路,而在星球的另一端,一些人正头朝下走路,钢铁可以飞翔,千里眼顺风耳是高科技,地球被我们称为生活,而整个太阳系里则挤满了未知的人和死去的人……
我喜欢这些与理智毫无关联的逻辑,喜欢神话胜过喜欢历史,历史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但真实的基础往往是谎言,只有神话能让我着迷。
在安徒生童话里,巫婆住在海底,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泥煤田,到处黏糊糊的,巫婆用白骨搭建房子,她正嘴对嘴的喂一只癞蛤蟆吃东西,水蛇在她肥大松软的胸口上爬来爬去。有一天。海底那个顶小顶美丽的人鱼公主找到她,小人鱼用海里最美的声音交换人类的双腿,巫婆割开胸口,让黑色的血液滴进药锅,喝下一罐沸腾的药,小人鱼疼痛得昏厥过去,鱼尾被分开,通往她命运的交叉小径也就此分开,她将得到王子的爱,拥有一个不灭的灵魂,或者变成一堆泡沫,在太阳升出海面的时候魂飞魄散。
相比之下,中国式传奇的结局更加清晰,皇帝宠爱一个女人,她是狐狸精,最后只能被一刀劈死,面若桃花的白蛇动了凡人的心,从此被镇在雷峰塔下……
苦于没有证据,我无法证明这些传奇中的真实成分,也无法证明终于有一天,我会长出一条尾巴来。传奇中充满了隐喻,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个我,其实并不是我,那是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比喻。
传奇会提醒我,世界上充满了饥饿和动人的灵魂,它们在相互寻找。
当人群挤在一起,我总会感到饥饿,我吃掉大量梦境和神话,是为了寻找和我一样饿得要死的灵魂。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