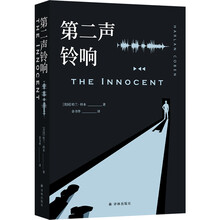到达延安之后,我们住进了石窑宾馆。
冷雨稀稀拉拉地掉下来,不过很快就停了。举头看天,大朵大朵的乌云不见了,灰蒙蒙的一片,好像天本来就是这种颜色,那曾经湛蓝的天,似乎被替换掉了。
第二天,我们驾车继续朝北推进。
在延安县境内,由于一列火车和一辆汽车相撞,我们直到天黑才进入李渠镇。寻了一家宾馆,把其他人留下来,我和祝天抒乘车进入山区。
土路,汽车开始颠簸。
四周黑咕隆咚,都是连绵起伏的荒山,有的地方裸露着贫瘠的黄土,有的地方突兀地冒出来一丛丛黑糊糊的植物,看上去疤疤瘌瘌。只有眯眼仔细看才能发现,半山腰上偶尔有一两户人家,亮着幽暗的灯。
拐了一个弯,车突然灭火了,世界一下安静下来。
我说:“天抒,你看,那里有一户人家!”
祝天抒看了半天,终于捕捉到了那团弱弱的光亮,她冷静地问:“那是……人家吗?”
我拽开金杯车的门,一股寒风就灌了进来,我说:“走,我们去问问路。”
她跳下车,警觉地向四下望了望,然后走上来,握住了我的手。
天很冷,我穿着一件军绿色棉袄,她只穿着毛衣。老话说,十层单比不上一层棉。不过,她抓住我的手,并不是因为冷。在如此陌生的荒山野岭中,四周伸手不见五指,根本辨不清东南西北,到处都埋葬着尸骨……别说一个女孩,我的心里也缺乏安全感。
我们走近了山路旁的那户人家。一座矮趴趴的房子,破旧不堪,窗子挡着玻璃和塑料,透出幽幽的光。我敲了敲门,用我掌握的半吊子陕西口音大声问:“师傅,门沟村怎么走?”
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妇女露出脑袋,警觉地看了我们一眼,又把门关上了。我面对闭门羹愣了愣,只好拉着祝天抒离开。
郝师傅已经把车发动了,我们钻进去,继续朝山里开。
祝天抒一直静静地观望窗外,她的身体在微微抖动。实际上外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
我要把棉袄脱给她,她不要,我就抱住了她的肩,想调和一下压抑的气氛,就说:“你在媒体上见到的周德东和我本人有什么不同?”
她转头看了看我,说:“你比照片还瘦。”
我说:“不过你别怕,我也服过役。如果遇到危险,你先撤,因为我退伍的时候只是一名上士,而你现在已经是中尉了。”
沿着凸凹不平的山路,我们的车行驶了半个多钟头,前面惨白的车灯里,终于出现了一个活人,他很瘦小,吃力地朝上走。
我吩咐郝师傅停了车,然后打开车窗问道:“师傅!请问门沟村怎么走?”
这个人三十岁左右,脸色黑黑的,两只圆眼睛,小嘴,周围的胡子乱七八糟。他操着浓郁的当地口音,又问了我一句什么。看来,不但我听不懂他,他也听不懂我。
我大声说:“我问你——门,沟,村,怎么走?”
他呜里哇啦说了半天,我还是听不懂。
祝天抒掏出纸和笔递给了我,我马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门沟村”三个字,举起来,用手电筒照亮,给他看。
他朝前指了指,好像说:前面就是了。
我又在纸上写了两个字——“古墓”,给他看。
他端详了一阵子,摇了摇脑袋。我不知道他是不清楚古墓怎么走,还是不认识这两个字。他可能只认得他居住的村名。
祝天抒太机灵了,又从旅行包里掏出我们买的一些古墓方面的书递给了我,上面有很多古墓图片。
我接过来,给这个人指了指上面的一张古墓图片。
他的眼神马上变得警觉起来。我当时甚至冒出了一个非常滑稽的想法——这个人会不会是一个伪装成当地农民的警察呢?
祝天抒把我也教聪明了,我从挎包里掏出一本我写的书,上面有作者照,举给他看,让他知道我是一个作家,然后我大声对他说:“我们来采访!”
他迟疑了一下,伸出胳膊划了一圈,意思应该是——四周的山上都是古墓。
我回头看看祝天抒,小声说:“我想跟他说,让他给我们带路,这个意思太复杂了,很难表达清楚。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祝天抒想了想,说:“钱。”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0元的人民币,大声对这个当地人说:“北山!你的带路!谢谢!”
这个人毫不犹豫地接过钱,然后就上了我们的车,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郝师傅在他的指引下,一直把车开到了山上。
停车之后,我和祝天抒每个人拿着一只手电筒,跳下来。
山上吏冷了。土路两边荒草丛生,稀稀拉拉长着一些叫不出名的矮树,只剩下干枯的枝权。四周有一股纸灰的味道。
古墓在哪里?
我走近那个当地人,大声说:“你带我们去找找!”
他说了几句当地话,显然还是互相听不懂。我拉起他粗糙的手,朝旁边的草丛里走,却被他一下甩开了。这个人看起来很瘦小,这一甩才让我感觉到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力道。毫无疑问,他明白了我的意思,借着车灯的光,我发现他的双眼里射出
没办法,我只好拽着祝天抒走进草丛,触目就是一个黑洞洞的墓洞,上面覆盖着密匝匝的荒草,简直就是一个陷阱,不小心就会摔下去。
我用手电筒朝里照了照,墓洞底的黄土上,竟然有一个残缺不全的瓦罐。
继续朝前走,我发现三步一个墓洞,五步一块尸骨,阴森可怖。
尽管如此,我依然不理解刚才那个当地人的反应。按理说,他从小就生活在这一带,对这些古墓应该麻木了,为什么还那么害怕呢?
我紧紧抓住祝天抒的手,生怕她一脚踏空,掉进哪个墓洞里去。我们没有铁锹,万一有人掉进去,引起塌方,救都来不及,等于活埋了。
我们在古墓上慢慢地行走,一直没找到刘明久说的那棵系着白布的树。
我回头对祝天抒说:“现在害怕吗?”
她笑了笑说,“不怕,真的好像来做客一样。只是这里太静了,没有人接待我们。”
她的话音未落,突然在荒野里响起一个尖利而古怪的声音:“都在地下呢!!!”
祝天抒惊叫了一声,一下就抱住了我。我也抖了一下,本能地举起手电筒,照在前面一个人的脸上——肤色黑黑的,两只圆眼睛,小嘴,周围的胡子乱七八糟——正是那个当地人!
他发出这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后,后退一步,“扑通”一声就跳进了一个黑洞洞的墓洞里。
祝天抒拽了拽我,要跑回车里去,我却死死拉住了她,没有动弹。
我在紧急地思考。
这个人不是一直跟着郝师傅站在山路上吗?他怎么突然绕到我们前面来了?
这个人不是只会讲当地话吗?尽管这句“都在地下呢”也不算是普通话,但是谠得清清楚楚,字正腔圆,谁都听得懂!
另外,他叫出的这句话,为什么跟我梦见的一样?为什么跟刘明久半夜里听到的一样?
这不是小说,我亲爱的读者,这是现实!
我只能这样想:也许,刘明久早就通过电子邮件向我提供过这条恐怖线索,我看了,只不过马马虎虎没记住,而“都在地下呢”这句话却埋进了我的潜意识里,于是我夜里梦见了那样的情景。站在刘明久家窑洞窗户外的那个拎灯笼的影子呢,其实就是刚才跳进墓洞的人……
这样一梳理,逻辑就清楚了。
可是,这个人是谁!
他为什么出没在这片古墓里?我们采风在山路上只遇到一个人,为什么偏偏就是他?现在,他到哪儿去了?
祝天抒颤颤地说:“周老大,他,他到哪儿去了?”
我拉着她,朝前逼近一步,站在了那个深深的墓洞边缘,用手筒朝里照去,这个墓洞纵向大约有四五米深,底部有一个横向的深洞。
我回头对祝天抒说:“这地下的墓道很可能是相通的,过一会儿,说不定他就从哪个墓洞里冒出来了。”
祝天抒的口气突然冷静了许多:“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说:“回车上吧,明天白天再来探访。”
祝天抒说:“好。”
我拽着祝天抒小心地躲过一个个墓洞,朝山路走去。
郝师傅在抽烟。他已经把车熄火了,只看到一个烟头在黑暗中闪烁。
来到山路上之后,我依然提心吊胆,总觉得脚下有深坑。我有一个战友,他在南疆打过仗,敌人最擅长埋地雷,每走一步都可能被炸上天。直到他从前线撤下来,退伍回家,走在柏油路上,仍然不放心,总觉得一脚踩下去就会爆炸……现在,我理解他的那种感受了。
我紧紧拉着祝天抒的手,在距离抽烟人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来,一边细细观望他的脸一边问:“是郝师傅吗?”——在这个地方我谁都不相信了。
郝师傅踩灭烟头,大声说:“你们回来了?”
是他,我们的司机。
我四下看看,问:“那个当地人呢?”
郝师傅说:“刚才他突然就走了。我想着,反正下山的路我也找得着,就由他去了。我们走吗?”
我说:“走,去门沟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