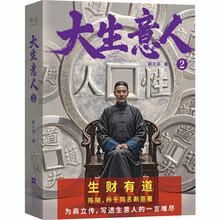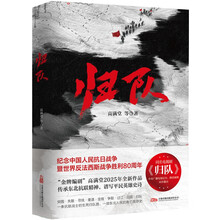一、筱燕秋天生就是青衣的坯子
今天是筱燕秋的19岁的生日。
筱燕秋在家里面排行老五,母亲在生她之前因为连着生了四个丫头,已经完全没有了金贵自己的理由,在临近生产的最后几个时辰她还拖着硕大的肚子,屋里屋外,房前房后,喂鸡喂猪地忙着。
太阳落山了,母亲焖好了小米饭,又用煮小米饭剩下的米汤炖好了豆角,她从咸菜缸里面捞了个咸菜疙瘩细细地切了丝点了香油,挑拌好。
母亲这次怀孕和前四次有些不同,肚子特别的大,腿脚还特别的勤快,她上蹿下跳,什么样的活都争着去干。俗话说,勤小子懒闺女。村子里面有经验的女人都断定她这次准能打个翻身仗。
饭菜刚刚从锅里面冒出香味,阵痛就由远而近地来了。母亲愣在那里,她盼这个时刻,更怕这个时刻。这个时刻来了,是福是祸肚子里面的这块肉总得出来见人。
她往灶里添一把火,冲院子里面刚刚赶鸭子回来的三丫头喊:“三丫,快到西头去把你刘娘喊来。”
三丫怔怔地看着她。母亲大声说:“发啥呆?快去呀。”
三丫撒腿跑了,鸭群大呼小叫欢蹦乱跳地追了出去。
母亲忍着疼把锅里面的饭菜盛出来,洗干净锅烧了一锅水。锅里面的水开了,母亲肚子里面的羊水破了。屋子里面蒸气缭绕,母亲气喘如牛,她挣扎着往炕上挪,离炕还有一丈远的时候她挪不动了,孩子已经挤出来了,两条小腿别在她的两腿之间。母亲急了,大叫着一使劲,孩子盘腿大坐地滑落在地上。
气喘吁吁跑来的刘娘被这阵势惊着了,两手往腿上一拍叫道:“我的娘亲,是个坐生!这样的胎位得到医院里面动大刀子,你真有种,能一个喷嚏把她崩出来!” 母亲看了一眼孩子,脸上的汗雨一样地淌落下来,她呻吟了一声:“她爹回来能打死我。”
刘娘安慰她:“这丫头多好,足有八斤半。”
母亲带出了哭腔:“千斤也不如那二两肉管用啊!”刘娘把孩子洗干净包好放在炕上说:“这孩子坐着莲花投生,没准是王母娘娘转世呢。”
母亲泪雨滂沱:“她咋不是哪吒转世呢?她要是脚踩风火轮手抡乾坤圈,我还怕谁?你说我还能怕谁?”
五丫头落地之后没哭两声就闭着眼睛睡了,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站了那么长时间怎么能不累?她不知道父亲回来后怎么修理了母亲。她看见母亲的第一眼就知道女人不待见她。五丫头一寸寸地蔫了,一节节地萎了,王母娘娘的水灵劲儿被一点点地风干了。嫩藕一样的胳膊变成了芦柴杆,油黑的头发变成了蒲公英的帽子,饱满的额头露了骨,房檐一样支在眼睛上面,两只眼睛像两口枯井敞着盖子由着臼晒雨淋。
这个取名叫筱燕秋的丫头不爱哭也不爱笑,那张嘴除了吃饭好像没有别的作用。她像条影子像个哑巴,有她不多,没她也不少。姐姐们不爱带她出去玩,村子里也没有女孩子来找她玩儿。
九冬九夏九来九往,筱燕秋九岁那年,牡丹城京剧团来村里面演出,筱家的五丫头像被坏人拍了花,不声不响地离家出走了。四天以后她回来了,连有雀蒙眼病的王奶奶都看出来五丫头不大一样了,好像这个五丫头是那个五丫头生出来的。说她是那个五丫头吧,处处都不像,说她不是那个五丫头吧,举手投足又处处露出那丫头的痕迹。这个五丫头的眼睛不是枯井是湖泊,头发不是枯草是丝绸,这个叫做筱燕秋的丫头片子,浑身上下处处渗透出和这个家庭完全背离的气质。这种陌生的气质把她的爹和妈逼到了墙角里。
筱燕秋说:“我跟着剧团走了。”父母还没醒过盹来,她又说:“我要考戏校!”她的语气沉着而坚定。母亲半张着嘴,父亲也半张着嘴,父母俩像看年画一样看着她,他们俩谁都不知道这个丫头在想什么。筱燕秋看着像呆鹅一样的父母加重了口气说:“如果不让我考,我就去死。”她把死这个字说得又硬又冷,像冬天河槽里面的石头一样冰人。
父亲想了三天,筱燕秋水米不沾牙地等了三天。三天后父亲同意了。筱燕秋苦苦地考了四年,四年啊,一个大学本科都读完了,这个丫头才勉勉强强地拱进了那所戏校。
从筱燕秋迷上唱戏到现在整整十年过去了,19岁的筱燕秋经过了一番脱胎换骨的蜕变已经成了一个对于她的父母和家乡来说完全陌生的姑娘。
母亲对筱燕秋说她是生在晚上8点,今晚的首场演出也定在晚上8点,等锣鼓点敲响,大幕拉开的时候筱燕秋就整整19岁了,这个l9岁是值得纪念的19岁。今天是筱燕秋分到剧团,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日子,尽管是跑宫女,那也是作为国家正式演员的登台亮相。生日和登台亮相是老天爷送给她的两份厚礼。
今天晚上筱燕秋有点莫名的紧张。刚刚分到京剧团半个月,跟谁都不熟。她坐在化妆间刚打上底色,比她早一年分来的戏校校友,唱老旦的裴锦素指了指墙上挂着的黑板说:“姐们儿,今天轮你值日。”
筱燕秋慌忙站起来拎起茶壶往外走,她知道演出水是第一不可少的。
这座剧场是老式的俄罗斯建筑,走廊很宽,顶子很高,冬天热,夏天凉。
牡丹城的气温在一场一场的秋雨里凉了下来。绵长的雨丝天上地下腻腻歪歪地拉着扯着,撕着拽着,扒光了人身上的暑气。
这天晚上文化宫如同往常一样座无虚席,放映孔里面射出来的一道耀眼的光柱,投在舞台上悬挂着的银幕上。震耳的锣鼓点声从舞台两侧的喇叭里面发出来,在剧场里面萦绕回荡。银幕上穆桂英佩甲扎靠带领杨门女将们提缰带马,跟随余太君直奔沙场。
银幕后面热闹异常,市剧团里面的20岁的老旦演员裴锦素身穿毛衣,脚穿练功鞋,领着一群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们在宽大的戏台上跑着圆场,她们跟着银幕上的人物,熟练地一招一式地比划着。姑娘们的表情庄严肃穆,嘴一张一合跟着片中的人物无声地唱着。看得出这部电影她们至少看过了十几遍,已经倒背如流,熟记于心。
观众们没有人知道后台在做什么,他们完全被剧情吸引住了。好戏总是觉得短,观众们还没尽兴,一个大大的“完”字已经映在银幕上。这时后台的灯亮了,女孩子们追逐嬉闹的身影被灯光映在银幕上。舞台监督从边门跳到舞台上吆喝了一嗓子:“不去化妆,闹什么闹?”女孩子们吓得噤了声,一窝蜂似的涌进后台化妆室里面去了。舞台监督耀武扬威地又喊了一嗓子:“装台!”舞美队的小伙子们蹦上台,手脚利落地干起活来。
文化宫门口的广告牌子上面写着《三岔口》、《贵妃醉酒》、《钓金龟》等几出折子戏的戏名。广告牌子下面人头攒动,吵吵嚷嚷。售票的窗口处挤满了人,拥挤推搡,秩序非常混乱。
后台的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老服装员钱双喜把戏装熨烫平整,一套套挂在服装架子上,他把皂靴和绣花鞋一双双整整齐齐地靠墙摆放在地上。秃了顶的老琴师坐在一旁慢慢悠悠地抽烟、喝茶,听着身边的半导体,半导体里面正在播送有关科学的春天的报道。
大化妆室的墙上挂着块值日黑板,上面写着“筱燕秋”三个字。
女孩子们身穿水衣,坐在镜子前面打底色化妆。裴锦素对着镜子往老旦妆上画着皱纹。
武行的师傅边给二弟子勾脸边说:“这勾脸是学问。我勾的这脸上有工笔有写意,还有随情随性带出来的东西。我手里这支笔就够你们琢磨一辈子的。”
对着镜子自己化妆的大弟子往这边瞥一眼。武行师傅不看他:“你们都给我记住,人物不在脸,而在于心。脸上的红黑,不过是衬托人物的心地,把人物的美丑透出来而已。记住没有?”
两个徒弟同声回答:“记住了!”
裴锦素戴好头套,对着镜子“嘿嘿”傻笑。张慧芝白了她一眼:“脸画得像颗虎皮蛋似的,有什么可笑的?”
裴锦素:“20岁的裴锦素碰到了60岁的裴锦素,我开心!我痛快!”
于静揭发她:“你是笑裴锦素这三个字终于爬上节目单了吧?”
裴锦素眉开眼笑:“你看出来了?”她笑嘻嘻地唱道:“瑞雪纷飞,人欢笑,分衣分粮,庆翻身……”
老演员柳如云把头发解开盘好,用黑色的丝巾包住,她心闲气定,认真地净面、润肤、铺底色。
武行师傅领着两个徒弟站在服装架子前。
钱双喜问:“老大先穿?”
武行师傅伸手拦住他:“您甭动手。”他转身对大弟子说:“你师弟今天是角儿了,你给他上行头。”
二弟子一脸喜色,拉着武行的身架子,等师兄给他穿戏装。师兄忍气吞声地给师弟穿衣,套靴。武行师傅认真地给二弟子束冠。钱双喜抽着烟有滋有味地看着。
武行师傅对大弟子说:“过去他给你端饮台,今儿轮你给他端了。”
大弟子接过师傅手中的饮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
钱双喜拍拍两个小武行的肩膀:“好好唱,你们师傅那儿预备着酒呢。谁的活儿好,谁有出息,他给谁喝。”
裴锦素说:“咱们团准备上新戏了。”
女孩子们顿时来了情绪:“上哪出戏?”
裴锦素憧憬道:“不知道,要是上《杨门女将》就好了,佘太君非我莫属。”
张慧芝一撇嘴:“魏团长是你亲爹啊?”
柳如云用指尖顶住自己的眼角,把眼角吊向太阳穴的斜上方,开始画眉毛,画眼睛。
裴锦素:“他不是我亲爹,也得从心里承认,我的嗓子是团里数一数二的好嗓子。”
张慧芝:“咱们团没有好老生,拿什么排新戏?”
裴锦素:“谁说咱们团没有好老生?魏团长当年红透半边天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呢。”
柳如云用中指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眼框、鼻梁画红了。拍定妆粉,上胭脂。
张慧芝:“好像你听他唱过似的。”
裴锦素说:“我妈和我爸听过。他们说,20年前,魏笑天这三个字在牡丹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柳如云仔细修改着画坏了的眉毛。
于静叹了口气:“当初我要是学老生就好了,省得现在天天混在丫环群里跑龙套。”
裴锦素:“那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你得有唱老生的本钱。”
于静不高兴了:“就你有本钱!”
裴锦紊得意洋洋地笑,她用老旦的韵白说:“本钱么?丫头,来!来!来!老身让你开开眼……”她站起来,凌空一个大跳。落地后,摆了个造型唱起来:“穿林海,跨雪原……”
正在听半导体的老琴师,脑袋不由自主地随着裴锦素的唱腔摇晃起来,他摇得不解气,一把抄起身边的京胡,嘴角叼着烟,跟着裴锦素的唱腔,抖弓,摇头晃脑地使劲拉起来。
值日的筱燕秋拎着开水壶走过来。
裴锦素一口气唱上去:“气冲霄汉……”她的嗓子高亢激越,极具穿透力。女孩子们鼓掌、跺脚、叫好。
走廊里传来团里当红青衣李雪芬一声清脆的叫板,化妆室里顿时安静下来。裴锦素伸了下舌头悄悄坐回到椅子上。
女孩子们坐在镜子前面,老老实实地勒头、描眉、贴水片。
化好了妆的李雪芬,身着水衣,从单人化妆间里慢慢地走出来。筱燕秋和她打了个照面,李雪芬像没看见筱燕秋一样,扬着头从她身边走过去。筱燕秋回头看她。
李雪芬伸展双臂站在服装架前,钱双喜殷勤体贴地把戏装按规矩,仔仔细细地给她穿上。李雪芬伸脚,钱双喜把绣鞋给她套上。李雪芬的一举一动充分体现了一个名角儿的派头。筱燕秋拎着水壶站在一边看傻了。
跟班把一缸子晾好的水递过来,李雪芬翘着兰花指,仔仔细细地润了遍喉咙,开始“咿咿呀呀”地喊起嗓子。
筱燕秋想起来自己的任务,拎着水壶转身朝化妆室跑去。
武行师傅活动完腰身,把腿放在墙上压。两个徒弟站在旁边恭恭敬敬地看着他。
武行师傅:“我们学徒那时候,一进师傅门就得直溜溜地站桩,耗腰、耗腿。天热了。拿蝇甩子轰苍蝇。天冷了,拿对刀耍刀花。为的是耗膀子。花脸的功架全在腰上、膀子上、脖子上。”
师兄和师弟互相看了一眼,争先恐后地把腿举到墙上玩命地压。
女孩子们化好了妆,往手背上涂底色。
筱燕秋挨个给化妆台上的每一个杯子里面倒满水。筱燕秋倒水倒到柳如云的化妆桌前,她发现柳如云的桌子上面没有水杯。她找了一个杯子,刷洗干净,倒满了水恭恭敬敬放在柳如云的面前。
柳如云绷着脸把水杯推开,掏出钥匙打开身边人造革包上的小锁。筱燕秋不解地看着她。柳如云从包里拿出来自己的水杯,放在桌子上。筱燕秋明白了,她拎起壶刚要往杯子里面倒水。柳如云两手紧紧护住杯口,厉声喝道:“别动!”筱燕秋吓得一激灵。化妆室里的人纷纷往这边看。
柳如云阴沉着脸,端着杯子自己打水去了。
筱燕秋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愣了一会儿神,忐忑不安地把地上的脏东西扫到一起。她看到~只杯子紧贴着桌子边放着,就顺手往里面挪了一下,接着低头扫地。
柳如云突然一声尖叫:“站住!”筱燕秋抬头看。
柳如云的兰花指直戳到她的鼻子尖上:“谁让你动我的水?”
筱燕秋吓了一跳,她怯生生地看着柳如云。
柳如云:“杯子把本来朝左,你没动,它怎么朝右了?”
筱燕秋小声回答:“怕洒了,我往里面挪了一下。”
柳如云两眼冒火:“你喝了!”
筱燕秋分辩:“我没喝。”
柳如云双眉倒竖,“啪”的一声,把杯子狠狠地摔在地上,她指着筱燕秋的鼻子尖,厉声喝道:“你倒想喝!你熬到我这戏份上了吗?”
筱燕秋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我……”
演员队长王国祥跑进来:“怎么了?怎么了?”
筱燕秋的眼泪围着眼圈转。
王国祥看看柳如云,看看地上的碎杯子,他明白了。他抢过来筱燕秋手里的扫帚把碎杯子扫了。柳如云气哼哼地坐下。
王国祥对筱燕秋说:“快化妆去。”
筱燕秋红着眼圈坐在那里化妆,裴锦素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化妆桌上。
裴锦素说:“别理她!这老妖精就这德行!”
筱燕秋:“她凭什么这样对我?”
裴锦素:“她这人眼里除了自己根本就没有你我之分。不是对你,她对谁都这样。记住,以后离这老东西远点。”
筱燕秋气乎乎地往脸上涂胭脂。
裴锦素压低声音:“别看她像个鬼婆似的整天闹妖,50年代她可是戏剧舞台上最著名的美人。你知道咱们团的《奔月》吧?”
筱蒸秋点点头。
裴锦素:“她就是当年的那个嫦娥。”
筱燕秋吃了一惊:“她?”
裴锦素:“只可惜这个嫦娥还没来得及舒广袖,就从天上摔下来了。公演前一位领导看了内部演出很不高兴,说,江山如此多娇,我们的女青年为什么要往月亮上跑7这句话把剧团领导的眼睛都吓绿了,《奔月》当即下马。柳如云一急,嗓子倒了。她一口咬定有人嫉妒,下药毁了她的嗓子。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