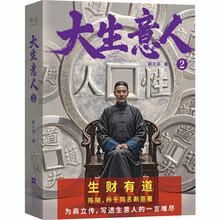1
翟耀东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段话:二十岁的男人半成品,三十岁的男人是成品,四十岁的男人是精品,五十的男人是极品,六十岁的男人是上品,七十岁的男人是废品,八十岁的男人是纪念品。翟耀东今年刚满四十岁,正处在精品男人阶段。
精品男人翟耀东没结婚,是个连正经恋爱都没有谈过的童男子。
如果从二十五岁开始有人介绍对象算起,两个月见一个,十二除二等于六,十五乘六……如此推算下来,翟耀东已经见过九十个有可能成为他老婆的女人,还差十个就进百了。总有一天,他会拉着一个女人的小手告诉她说:“你是我的百里挑一。”
翟耀东是个有梦想的人,白天无法实现,就在梦里继续努力。这一天,他又做梦了,梦见自己攀着绳子上了墙,健步如飞地在墙上走。
墙下是自己的家,窗子里面目不清的老婆和面目不清的儿子在温暖的阳光下吃饭。一个蒙面人突然破门而入,他闯入得太突然,翟耀东猝不及防,脚一滑,仰面摔躺在墙头上。翟耀东举起来手里的DV机拍摄下来蒙面人的整个犯罪过程。
DV机里老婆拿出来一兜子钱,一万块一叠,十好几叠。劫匪不满意,他用胳膊狠狠地勒住老婆的脖子,老婆挣扎着扭过脸冲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喊起来:“耀子!耀子!”
翟耀东想下墙,发现上墙用的绳子被母亲收走了。老太太用那根绳子在院子里晾衣服。
“妈!妈!你快把绳子递过来!”
翟母听不见儿子的喊声,她把蕾丝胸罩、短裤和孩子鲜艳的衣裳一件一件搭在绳子上。翟耀东急得冷汗直流,他用手指抠着墙缝,壁虎一样爬上屋顶,又从屋顶爬下去。他脚踩窗台,顺着窗子弹射进屋子里。蒙面人松开他的老婆,掏出来手枪,动作漂亮地耍了个枪花,抬手就是一枪。弹头发出刺眼的光,旋转着冲着翟耀东的瞳孔飞过来。子弹裹着风声的啸响里飘出来一个男人甜腻腻的歌声: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阳光在翟耀东的脸上爬行,暖得人发痒,他的眼皮哆嗦了几下醒了。他翻了个身,不情愿地睁开眼睛,电视里一个男票友正翘着兰花指在唱旦角。
翟母把干净的内衣内裤拿到儿子的枕头边上说:“这么喊你,都不醒,看看几点了?”
翟耀东看了一眼手表,差十分九点,他慌忙爬起来换上衣服。几天前他在都市生活报上登了一个征婚广告,跟几百个等待挑选的男人挤在一个二指宽的夹缝里。压在他身上的不是博士就是硕士。介绍他一共用了二十几个芝麻粒大小的字:B252年龄四十岁,身高一米七六,体重七十五公斤,职业,公司职员,未婚。字太小,眼神不好的,得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昨天,他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约他十点钟在觅渡桥旁边的超市门口见面。
翟耀东的家是一所老式的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外加一间违章盖出来的厨房,面积大约60平方米。卧室翟母住,客厅里靠墙的地方,用三块木板架起来一张床,翟耀东在这张床上一睡就是几十年。他不觉得委屈,翟耀东有个特点,从来不跟比自己强的人比。没有比上不足,那么就永远比下有余,所以他胸膛里那颗跳了四十年的心脏依旧红润细嫩充满弹性。
翟耀东在厨房里洗脸,翟母在旁边倒水挤牙膏伺候他。翟耀东长得不像母亲,他是墙上父亲那张遗像的拷贝。翟母个子矮小,皮肤细腻,鼻梁高挺,看得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个有些姿色的女人。
翟母二十岁的时候嫁给了翟耀东的父亲,先后生了女儿翟春红和儿子翟耀东。翟耀东的父亲体弱多病,四十不到就让老婆守了寡。翟母靠一个月三十二块钱的救助金把一对儿女拉扯成人。
翟母不识字,她的是非判断全部来自戏曲中的戏词。女儿翟春红违背母愿嫁给海员去了外地。翟母伤心了一阵过去了,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翟耀东是她一寸一寸养大的,在她的眼睛里,全世界的没有一个女人配当她的儿媳妇。谁嫁进翟家门,她的儿子都吃亏。翟耀东见过九十个女人,其中五十个是被母亲一苍蝇拍子“拍死”的。另外的四十个是对方没看上他。
翟母不服输,撇着嘴说:“没看上我儿子的女人,是没有眼光的女人。”
墙上挂满水渍的镜子里映出来翟耀东的脸,翟母看着镜子里的儿子问:“今天要见的那女的在哪儿上班?”
翟耀东努着嘴把脸上的肉扯到一边,仔细刮着腮帮子上的胡子茬。
他嘴里“呜噜”了一声。
“嗯?”
翟耀东擦干净脸上的肥皂沫子说:“医院。”
翟母满意地“哦”了一声。
翟耀东坐在饭桌上,一只手操遥控器换了电视频道,另一只手接过来母亲剥干净皮的鸡蛋一口塞进嘴里。
电视里一个民工打扮的女人,偷偷摸摸地往地上和电线杆上贴小广告。
主持人说:我们要坚决杜绝这种影响市容的不文明行为……此新闻由本市居民翟先生提供。
翟耀东得意地笑着露出来嘴里的鸡蛋黄,他说:“一条这样的新闻二百块,《社会写真》要是一个星期能用我一条新闻,每个月我就能多挣八百块钱,比拼死拼活地长一级工资合算得多。”
“昨天来人测量房子了。”翟母说。
“你跟我说两遍了。”
“我说八遍也不见你着急,多一口人,多十个平方米呢。你早晚也得娶老婆生孩子不是?现在不赶紧定下来登记了,面积一点没得着,以后咱娘俩的房子还得祖孙三代四个人住,这么一想,心里都亏得慌。”
“我知道。”
翟耀东穿好衣服往外走。
“去那么早干啥?显得多没身份。”
听母亲这么说,翟耀东放慢了穿袜子和鞋的速度,他站在立柜的镜子前面把白色的棒球帽扣在脑袋上,又把微型DV机系在腰间。
翟母皱着眉头打量着他:“戴这么顶孝帽子多难看?”
翟耀东把帽子摘下来,看了看又戴上了。戴这顶帽子是昨天在电话里定好了,这是女方辨认他的一个明确标志,母亲有意见他也不能搞了。约会地点在觅渡桥的超市门口。那女人在电话里告诉翟耀东,她穿一身黑衣服,打一把黑伞。
翟母不喜欢女人这副打扮,说:“一身黑?听着就丧气!”
那女人的声音低沉圆润,沉浸在她的声音里不由得不产生在太空里坠落的幻想。别说穿着一身黑,她就是披麻戴孝,翟耀东也会冒死去见她一面。
相对象这件事叫翟耀东又爱又十艮。爱的是,每一个女人都是新鲜不可知的;恨的是,每次见面,女人们总是往费钱的地方领他。不去,显得不男人。去了,活生生地让她啃一顿,肝疼肉颤不说,回家交不上账,老太太唠叨得胜过唐僧。妈是为自己好,这点他心知肚明。
翟耀东在文化宫下车转乘35路,车还没有到,他仰着脑袋看站牌上的站名。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挽着丈夫的胳膊絮絮叨叨地说着家务事,男人眼睛盯着站牌心不在焉地听着。
35路车来了,翟耀东夹在人群中挤上了车。车门在售票员的大声吆喝中关上了,司机发动了汽车,35路车缓缓往前开动,司机在后视镜中看到一个女人跟着汽车拼命奔跑,她边跑边使劲拍打着后车门。司机踩了一脚刹车,打开了车门。女人跳上汽车,靠在车门上气喘如牛。
售票员大声说:“刚上车的乘客请往里面走!”
女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手拉着扶杆一使劲,离开了车门,钻进了车厢里。
这个女人名叫邓佑真,今天对她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她要去交二手房的首付。从娘肚子里爬出来长到四十岁,这是她第一次有自己的家。没结婚前,家是父母的家。结婚以后,家是丈夫的家。对父母来说,她是嫁出去的女。对丈夫来说,她是离了婚的老婆。在哪个家里她都是外人。俗话说的好: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坑的萝卜是自卑的萝卜,她得好歹找一个坑把自己这根萝卜栽进去培上土,黄土埋半截,说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车厢里很拥挤,邓佑真被不断上车的人挤到了翟耀东的身后。
“没买票的请买一下票!”售票员伸着脖子冲着刚上车的人大声喊。
邓佑真掏出钱包,拿出来十块钱,递给售票员。售票员够不着,翟耀东顺手接过来钱帮忙递了一下。邓佑真瞪着眼睛,看着售票员给她找零钱。她的眼睛很大很黑,看上去有几分眼熟,这个熟藏在一个角落里,少年时期酸酸甜甜的感觉刚一露头,倏地一下又没了踪影。
汽车到站停下来,又上来了几个人,他们推推搡搡地把翟耀东挤到了跟他一起上车的那对中年夫妻中间。女人的个子不高,头发蹭着翟耀东的鼻子,她的头发上有一股子炒菜的油烟味儿。翟耀东涨着鼻孔想打喷嚏,嘴张了两下没有打出来。女人没有察觉丈夫被挤走,身边已经换上了另外一个男人。她的手很自然地插进翟耀东的臂弯里。翟耀东的脑袋一下子空了,心跳出来拖拉机开动的“突突”声。他鱼一样地张着嘴,眼皮抖得不敢往起抬。翟耀东垂着眼皮,眼珠顺着胳膊往下溜,他看到了一只白胖的手。这只手手指粗短,手背上面旋着五个很深的肉坑。
“一会儿咱俩到超市买点肉馅。”女人眼睛看着窗外。
翟耀东舌头根儿发硬,唾沫干在了上牙膛子上。那只胖手松开了他的胳膊,伸到他耳边,缠绵地攥住了他的耳垂,轻轻揉搓了一下又一下,翟耀东的脑袋“嗡”的一声冒出了金属声,身上的汗毛齐刷刷地站立起来。他的耳朵小时候被母亲掏耳朵的时候摸过,那个摸跟这个摸的性质截然不同。这个摸很霸道,里面藏着一种不地道的东西,弄得他突如其来地尿紧。
女人说:“我妈做的馅好吃,晚上叫她给咱们包饺子吃。”
翟耀东闭着眼睛咬着牙,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抽着凉气。男人听到老婆说话,他没有搭腔。女人的手加重了力量,她狠狠地捏了一下翟耀东的耳垂。
“一说去我妈那,你就装哑巴!”
这只胖手劲儿真大,翟耀东疼得头一甩,脑袋砸在身边那个男人的太阳穴上。“咚”的一声闷响,两个男人“哎呦”叫了一声,同时捂住了脑袋。
女人发现自己捏错了人,吓得惊叫了一声:“妈呀!”
她的叫声很大,引得车厢里的人纷纷回头看。男人捂着脑袋扭过头看他老婆,他的老婆脸蛋青中透紫,翟耀东的脸蛋紫中透青。这一男一女神色慌张,喘息未定,模样十分可疑。
“怎么了?”男人虎着脸问。
女人红着脸看了翟耀东一眼,话翻上来又咽下去。男人抬手给了翟耀东一个耳光。
“吃我老婆的豆腐,瞎了你的狗眼!”
“你……”翟耀东后面的话没来得及出口,男人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冤枉”两个字从胸腔里进出来,横卡在喉咙口。翟耀东站立不稳,朝后面倒去。乘客们猝不及防,一个撞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惊叫着往后倒。车厢里大乱,男人揪住翟耀东的衣襟把他从地上拖起来。翟耀东使劲挣扎,触摸屏的手机从衣服口袋里掉在地上。翟耀东怕被人踩坏了,挣脱男人的手,趴在地上捡起来手机。男人看不见对手,急得一蹿一蹿地往高处蹦,他谢了顶的脑袋在人群的头顶上一起一伏潮涨潮落。
男人声嘶力竭地喊道:“是爷们儿,别往裆底下钻,有种,你给老子站起来!”
翟耀东捡起来手机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司机突然急刹车,车上的人往前一冲,翟耀东差点被扑倒。他左手紧紧抓住身前的栏杆,为了站得稳,拿着手机的右手又扶住了头顶上的栏杆。胳膊肘撞了邓佑真的脸一下,邓佑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句:“讨厌!”
“怎么开车呢?”乘客们七嘴八舌地骂司机。
司机把脑袋伸出去骂横穿马路的行人:“你不想活,别拿我当垫背的!”
行人低着脑袋急匆匆地跑过马路。
汽车在觅渡桥站停下,乘客们拥挤着下车,大家谁也不让谁。翟耀东和邓佑真同时卡在车门口,拥挤中,翟耀东的左胳膊无意间插进了邓佑真右肩背着的挎包带中,俩人挣扎着一起挤了出来。一个往东,一个往西,走得很急。翟耀东胳膊上挎着邓佑真的挎包带子拽得她一个趔趄,差点跪在地上。邓佑真使劲把挎包拽回来,紧紧抱在怀里。
她瞪着两只眼睛看着翟耀东,骂道:“抢劫啊!”
翟耀东说:“我不是故意的。”
邓佑真说:“你还想说在车上耍流氓也不是故意的呢!”
翟耀东憋的一肚子火被她撞了出来,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挎包带子,把她拽回来。
“谁耍流氓了?谁耍流氓了?”翟耀东脖子上的青筋绷起来老高。
邓佑真死命拽过来挎包带子,看到挎包的拉锁好好地拉着,她搂着挎包,狠狠地瞪了翟耀东一眼,转身走了。
翟耀东站在那里气哼哼地盯着邓佑真远处的背影,丧气!真他娘的丧气!早上做的那个梦肯定不是什么好兆头,果不其然,一出门就触了一连串的霉头。
翟耀东皱着眉头骂骂咧咧地上了超市的台阶,他一眼看到了站在台阶上的那个跟他约会的女人。
徐竞男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装,打着一把黑布阳伞,她扬着小巧的脑袋,挺着细长的脖子,目中无人地站在台阶中央。这女人皮肤雪白,黑白对比产生了如此强烈的视觉效果。翟耀东的胸膛里“滋啦”一声响,滚热的烙铁熨烫过去,胸中所有的不快都被熨得平坦舒展了。
徐竞男用一身黑告诉前来赴约的人,她不是来搞对象的,她是站在新的约会地点上,凭吊她失去的青春岁月。她要给跟她约会的男人一个提醒,她不属于他的生活。可是她的脸,她的手,她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节都对翟耀东发出了难以抵御的呼唤。
徐竞男从墨镜上方盯着翟耀东,目光妩媚犀利。一块一块空白在脑海中跳跃而出,翟耀东在大脑短路的同时心脏也极度缺氧了。
“你迟到了四十分钟。”徐竞男的声音柔和动听,一点儿都不像责备。
“路上堵车。”翟耀东听见自己的声音挂着水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徐竞男摘下墨镜看着他,翟耀东的心被揪了一下,这是他见过的九十个女人当中最耀眼夺目的一个。徐竞男眼睛盯在他的脸上,两排浓黑的长睫毛上上下下刷了几下。翟耀东被她刷得心如擂鼓气喘不均,他在心里默念着一二三四五六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