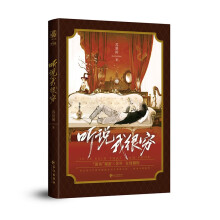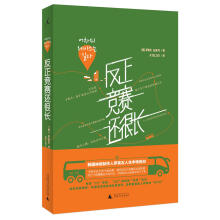我的小时候<br> 吵闹任性的时候<br> 我的外婆总是唱歌哄我<br> 夏天的午后<br> 老老的歌安慰我<br> 我记得<br> 是这样唱的<br> 天黑黑<br> 欲落雨<br> ——孙燕姿《天黑黑》<br> 最开始<br> 我真的以为<br> 歌唱就是飞的理由了<br> 迎着全世界怀疑的眼光<br> 我还是很倔强<br> 我真的以为<br> 我可以飞<br> 我叫菲飞,不漂亮,17岁。<br> 不知道多少女孩有过不漂亮的17岁,有不算苗条的腰,丰满的手臂,鼓鼓的小脸,算不上个胖子,但是也肯定不够瘦。一点儿也不像我那对身材挺拔苗条的父母。但至少他们把我养育得看起来很营养,很健康,活泼好动很招人喜欢。<br> 看了我现在的样子,没人会相信我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事实上我病得很重,差点死了。我的肾,被药水洗了不知多少次,那场严重的肾病差点夺取了我的生命。最后医生没办法了,对门口等着的家长说:“先用激素试试吧,要是还不能控制病情这孩子就得换肾了。”结果他们只能是点头。<br> 我活下来了,但那些激素让我变得一天比一天胖。<br> 那场病,把我变成了一个胖子。<br> 从上中学起,班里拿胖子开玩笑,总有人怪模怪样看向我。而我,傻乎乎地跟着笑。<br> 张帆说:“你笑起来真好听。”<br> 想了想,后面又加上一句:“挺没心没肺的感觉。”<br> 有了张帆,我的17岁过得不忧郁,即使不漂亮。他跟我从小学一路同桌到高中,还做了5年邻居,真正的青梅竹马。他说我没心没肺,所以他总要像个老母鸡似的替我操心。我觉得他大概是全世界最了解的我人,比我更会为这个叫菲飞的胖小妞做打算。<br> 高中毕业前一天,全班到卡拉ok道别,我喝了8瓶嘉士伯,抱着麦克风唱了一晚。<br> 他一路扶我回家,我跌跌撞撞,扯着他东拉西倒,终于两个人在路上跌成一团。地上是硬硬的沙石,但不疼,他是我的人肉垫子。<br> 我迷迷糊糊听到他说:“小飞,你的声音真性感,我想你在舞台上唱歌一定很好看。”<br>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性感,居然是他说的,真好真好。我抱住他,眼泪不可遏抑地涌出来。星光下,隔着我的泪看过去,他的眼睛亮得真璀璨。<br> 我们都知道,这是分离前的最后一次拥抱。<br> 毕业以后,我背个洗得发白的牛仔大包,拖着一个超大箱子跑到外地去考音乐学院;邻居张叔叔全家出国,而张帆去了一个更远的地方读大学。临走之前,我一个人跑去飞机场送他,隔着人群两个人手抓得紧紧的,真想永远永远都不放开。好像一放开,一部分自己就从此消失了。我们不是情人,可关于离别,大概所有的伤心都一样。<br> 音乐学院里有很多性感的声音。我第一次拉着行李走进学校的大门,那一刹,音符就像五彩烟花一样在耳边绽放开,小提琴、钢琴、小号、唢呐、笛子,还有一些一时分辨不出来的乐器声夹杂着高音,中音,低音,或浑厚磁性,或高亢清越的练声……一时间我完全被吸引啦!当我意识到自己即将在这个热闹而又高贵的地方生活四年的时候,我激动啦!打心眼里希望自己这个不起眼的小胖妞至少在这种环境里能够由内往外的突显出一些气质来掩盖外在的无光。由于想得太多,一不留神,我在无数“咪咪——吗吗——”的练声中迷失了方向,晕头转向,找不到地方。<br> 迷迷糊糊记得,有个背着吉他的男孩,晒得黑黑的皮肤,干净的衬衫,他接过行李把我一直带到宿舍门口。<br> 他的友好让我几乎想当场唱起来。<br> “你叫菲飞,社音系的?”他看了看我的的宿舍出入证。<br> “嗯。”我大概忘了说谢谢。<br> 他宽容地笑了笑:“我作曲系的,等有机会我给你写首歌,你来唱吧。”<br> 哇,随随便便就写首歌送人!我被音乐学院的艺术气氛震撼了,听话地一个劲点头,他似乎很想摸摸我头顶,不过最后还是没有这么做。<br> “再见,菲飞。”他朝我挥了挥手。我终于反应过来,还没问过他叫什么名字。<br> 新生入学都要选修一门副专业,我选了琵琶。当然不是因为它和我的身材很相称,选它是有原因的:我从小爱唱歌爱跳舞,自己在家开小型演唱会都至少是两个小时,上幼儿园时总被老师拉去办公室表演,后来就跑到学校的联欢会上去跳,一次妈妈跑到学校去看,我正在舞台上组织着一小队同学,扭着小粗腰跳得不亦乐乎。妈妈当场就沉下脸来。<br> 回家以后,她说自己的女儿怎么就不像个女孩子?念念叨叨了不下一百遍,最后下命令说:“你要是真的喜欢唱歌跳舞,就先给我乖乖地学门乐器。楼上李叔叔以前是专业弹琵琶的,要不你跟他学琵琶去?”<br> 我喜欢唱歌跳舞,可我第一次拿到琵琶的时候,一点也不喜欢,而且还特别的讨厌。那块冷冰冰的木头,又那么重,完全没有舞台上的歌舞那么可爱。抱起来都很吃力就更不用说还要边抱着边弹啦!妈妈还给我买了很多名师弹琵琶的vcd,试图增强我对这块木头的友好度。说实话,那些名师确实弹得好!有时侯还能把我至少吸引个半小时乖乖坐在那里看着听着,甚至还暗暗地在心里发过誓要向她们看齐。可只要是家里没有人的时候,那些可怜的名师们就会被我偷偷换成A-mei,MariahCarey。看来我对流行音乐的热爱还是没有办法被民乐中的弹拨之王——琵琶所取代,那个冷冰冰的木头琴,完全没有舞台上的歌舞那么吸引我。妈妈又给我买了一台小录音机,用来听琵琶的教学带,可是我没用它听过几次琵琶曲,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把偷偷攒钱买的阿妹专辑放进录音机里,跟着边跳边唱。<br> 就算这样,被老妈的大棒逼着陆陆续续学了六年,楼上李叔叔也曾经夸我弹得蛮有天分,可惜天分和爱好,有时根本走不到同一条路上。<br> 大学的第一堂民乐课,我穿着一条巨肥的滑板裤,戴两个大得吓人的耳环,没化妆,是因为我还没学会。这身打扮,和我咋咋呼呼闯进门的架势,把教琵琶的老教授吓了一跳。<br> “你怎么穿成这样?”他一身严肃的中山装,所以有资本不客气地教训我。<br> 我对他装傻:“老师,有什么问题吗?长裤长袖,你的学生里最保守的就是我啦。”<br> 其他的同学都忍不住哄堂大笑。我在心里邪恶地开心了一下,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变着法儿和妈妈闹别扭。<br> 下了课,我没等他留我谈话,大步走出了教室。学校花园里到处都有谈情说爱的人,我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所以七拐八拐,进了最偏僻的一间琴房,坐下来边晒太阳边发呆。<br> 记得在老家的时候,张帆有时候会骑自行车带我出城。那座不大的城市外,青山连绵,千里不见人烟。因为曾经有人在山里失踪过,我们不敢深入,每次只爬最外面的几座山峰。<br> 坐在山谷里,我唱起外婆哄我时哼过的山谣儿歌,张帆坐在一边静静地听。<br> 古老直白的调子,像寂静的山林,简单中有种失去家园的疼痛,说不上来什么感觉,每次我都有大哭的冲动。<br> <br> “吧嗒——吧嗒——吧嗒。”我在琴房里心不在焉地练着基本功,想起那片山林,突然大声唱了起来。<br> 有人在门口鼓起掌来,“菲飞,又见到你了。”帮我拿过行李的男生,背着吉他站在门口,安安静静地笑了。<br> 乖女孩这种时候应该害臊的,可我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br> “碰见你怎么总是在我丢人的时候呢?”我把手里的荔枝丢一个过去。墙上贴着“禁止饮食”的告示,我当做没看见,大模大样带了一袋荔枝进琴房,现在满地都是它花瓣一样的外壳。<br> “我为什么总是碰见你最可爱的时候呢?”这话如果换个头发长长穿破烂牛仔裤的男生说,就很像花言巧语,但他说就不像。不仅因为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出众,还因为他笑得非常让人安心。我偷偷盯着他看,觉得他弹琴时手臂的姿态稳健有力,真是好看。想哭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个肩膀靠靠,应该是件不错的事情,我有点儿不良地想。<br> “你来这里,是想当明星吗?”他若有所思地问。<br> 我摇摇头。<br> 他诧异了一下,“那是想做音乐老师?”<br> 我还是摇头。<br> 他又笑了起来:“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br>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蛮大声音地说。<br> 可是他不怒,依然很温和地笑了笑:“不想说吗?那我就不问了。”<br> 我把琴放回琴盒,跨坐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其实我就想唱歌,因为喜欢。关于将来,我还没什么打算。”<br> 我发现,离开张帆以后,我变得更加不擅长为自己打算了。从来没想过教书,至于做歌星,是好遥远的事情,远得根本不用去想。虽然我也偷偷想过一点,如果能像阿妹那样,站在巨蛋里唱live,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真的真的想不到,远得像童年的我望着城外最高的山一样,很美,只是高不可攀。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