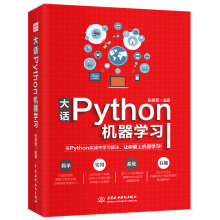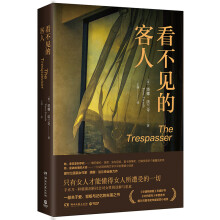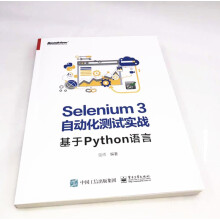第一章 黑松林营地
群山起伏,山峦叠翠。在一间由原木垒就的小屋里,郑汉亮蒙蒙咙咙地醒来。这里安详宁静,空旷山谷中流啭着鸟雀啼鸣。他微微地睁开眼,感觉到眼前是一片赏心悦目的翠绿,那样的恬美怡人。仔细一看,原来从东窗里射进一缕阳光,正照在铺边的木柱上。而那木柱,竟然爆出嫩枝新芽,还挂着几片新叶,嫩绿色的新叶宽硕肥大,沐浴在初晨的阳光中,通体透翠。
汉亮孩儿般甜甜地笑了。耳畔响起一首曲子,曲调优美又透出几分粗野泼辣:哎哟哟,我的妈,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插根筷子也开花,栽根扁担也发芽。哎哟哟,哎哟哟……
汉亮扭头看看边上,木屋里的统铺上,两个铺位已经空了,只有他和王明福还在睡。他推了推边上的小胖子说:
“明福,该起床了。老杨头和刘颐圳已经干活去了。”
小胖子翻了个身,嘟囔句什么,又睡了过去。
郑汉亮起床后,端着脸盆毛巾,到木屋后面的小溪边洗漱。溪边一块独立突兀的大石上刻着几个大字:黑松林营地。
树林里传来咚咚的斧砍树木声,精干瘦小的老杨头正在削砍栅栏木杆。郑汉亮顺道走去,身后已经背着袋囊、水壶,手里提一支老旧的7.62步骑枪。那是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人留下的,现在被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军垦战士用上了。
“去巡窖,汉亮?”老杨头问道。
“是,你又在扩建鹿圈?”
“待窖到新鹿,就有处安置了。”
老杨头从树枝上摘下一包挂着的东西,递给汉亮说:“这是我今晨刮的盐巴土,你把它撒在鹿窖坑的周边,夏天鹿就喜欢吃这个。”
汉亮接过后顺小道往山坡林子里走去。稍远了老杨头还在背后问道:
“他俩起床了吗?”
“刘颙圳已去蜂场了,王明福还在睡呢。”郑汉亮回道,便消失在树林后面。
一马平川的原野上,由远而近,渐渐地显出一支炮队,由一辆旧的美式吉普车带队,紧跟着一辆中型吉普,随后则是六辆解放牌军车拖着六门高射炮,在沙石公路上疾驶,逶迤出长长的黄色尘埃。
炮车队由西往东朝大山驶去,在山脚下的十五连营地停下来。满头银发的老团长邓明成从吉普车下来,对着前来迎接的连长林山清说:
“到你处借点云。”
“好哇,只要你做得成,我这一方天空任你耕云播雨。”
“我自有调云遣雨的专家。来认识一下,这是气象站站长陈原,还有我们的气象员韩琳珊。哟,琳珊呢?怎么没下车?”老团长问。
陈原同林山清握手后,对团长说:“她正在接收气象数据。”
吉普车内,韩琳珊戴着大耳机在一台大收发报机前记录着什么。边上仪器的指示盘上,红、蓝、黄、绿各种指示灯闪烁不停。琳珊观看着指示灯的数据,又核对着记录,在气象图上快速地绘制出一道道曲线。
陈原打开车门时,她已制作完毕,把气象图交给陈原后跳下车,一边拢着乌发,一边仰首眺望天空。这是一位异常秀美的姑娘,浓密的黑发衬着如象牙般白皙的脸蛋,两腮泛出青春的红润,清澈的明眸、细弯的秀眉以及那饱满的前额,显出一股隐隐约约的高贵和深邃气质。
“积雨云在生成,缓慢往西移动。”陈原看着气象图表,兴奋地说。
“看来琳珊推测是对的。”老邓团长对林连长说,“别看琳珊才20岁的姑娘,看云识天极准,是难得的人才。雨云何时到这里?”
“那要看它生成发育的情况。如果一切如愿,可能要到下半夜或明天清晨到达这里。”琳珊应道。
“要尽一切努力,让老天下点雨。小麦正处在灌浆时节,急需雨水。老林啊,这支炮队是用来人工降雨的,今晚就驻扎在你这里了。要打它一个伏击战。”
这是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行政编制为师、团、连,其实还是一个农场系统,日常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地处人烟稀少的东北北大荒地区,就从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调来上百万的知识青年,充实这里。古时称之为“实边”。这种制度最初始于中国两千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在边陲之地驻扎准军事人员,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进行战斗,所以又叫“屯垦戍边”。在连部的地形沙盘前,林队长在讲解这一带的山形地貌。这里地处完达山脉的南端,山脉南北走向,十五连位于山的西麓。山的东面是乌苏里江,称之为乌苏里地区,再东则是大海。韩琳珊认为大海中的寒湿气流遇到乌苏里地区的暖湿气流,会形成积雨云。此积雨云能否越过完达山脉,取决于山脉南端的兴凯湖。碧波万顷湖面的上空,经常出现涡旋状气流。如果气流呈逆时针状旋转则会推动积雨云越过完达山脉,反之则相反。
邓团长仔细地听着讲述。他要决定炮队在何处埋伏。因为必须要及时逮住越过山脉的积雨云,降雨才有可能。如逮不住,越过分水岭的积雨云就会被平原上的夏季风吹散。当然还要考虑炮车进出的方便,特别是一旦人工降下了大雨,炮队要能及时地撤出去。所以路况因素也得考虑。
“这个点是属于哪连的?”他指着沙盘上一处靠近主峰的特殊标志问道。
“这是我们连的黑松林营地。离这里有12公里山路,主要是经营人参种植、蜜蜂饲养和鹿茸加工副业。辟有一条简易公路到达那里。”
“好极了,炮队就设在那营地附近。”
于是准备出发,车辆已发动,林连长亦同行。他关照连部文书张勤道:
“给黑松林营地打个电话,通知他们要做高射炮人工降雨,防范鹿炸群。”
梳着两根辫子的文书张勤应道:“是,只是他们的电话不一定能打通。”
在密密的山林里,郑汉亮沿着一条隐约可辨的小径前行,不时攀缘突岩巨石,涉过山涧小溪,或跨过横树倒木。他检视一个个他们先前设好的窖坑。说是窖坑其实是陷阱。在鹿群常出没的地方,挖一个小室般的坑,上面架着几根拦腰锯断的木梁,再铺上干草沙土,枯枝败叶,浑然不露痕迹。上面撒着盐巴土和鹿喜欢吃的嫩树枝。鹿一旦走上这里,便会压断木梁,掉入陷阱中。
越过几个山岭后,他刚从一棵倒木跳过,发现前方的一个窖坑已经塌陷了。他高兴地三跳两跳跑去。坑里静寂无声,他扒开树叶,发现横梁断了,但鹿并没有掉进陷阱。他沮丧得直叹气。
待他修补好这窖坑,已是满头大汗了。他拍去身上的枯枝落叶,又继续赶路。攀上一道布满巨石的松树岗后,放眼望去,前方是波光粼粼、水连天接的大湖。湖岗上长满了针叶松林,沿湖畔延展的月牙形沙滩泛出银白色的光泽。这就是兴凯湖,由中苏两国分而辖之,中国据小半,苏联占大半。如这湖全归中国,则应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淡水湖。
汉亮欢叫着奔跑下湖岗,在银白色沙滩上甩掉了背囊、水壶、衣服,纵身跃人了清澈晶莹的湖水中。他欢畅地在水中嬉游,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时而蝶泳,尽情地消耗着青春富足的精力和体力。终于他累了,慢慢地游回了沙滩,扑卧在沙滩上,下半身浸在水中,任湖水拍打着他的脊背。
突然间,他看到眼前沙滩里有一块露头的陶片。他把陶片挖了出来,在水中洗刷。这是一块不小的残陶片,陶片上竟刻有一个人面像,眼、鼻、嘴俱全,嘴角下两侧还各有一个贯通的小孔。他把陶片洗了又洗。不时端详那图形,似乎想要解出它的含义。他起身观察湖岸沙滩的状况。久旱不雨,湖水退下许多。他竟然又发现多块鱼骨制品。片状,球状,均有贯通孔,可能是用作项链或胸饰配件。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包好放进背囊之中。
日头已偏西,汉亮离开湖畔沙滩,继续往山林深处走去。翻过几个山头,透过树林的间隙,他看到了一头鹿,一头健壮雄美的公鹿,美丽的三岔大茸角舒展在额首上。汉亮用桦皮哨吹着雌鹿的叫鸣声。公鹿犹豫着被一步步引入到汉亮的伏击圈内。终于轰的一声,伴随着树干的折断声和雄鹿的挣扎嘶叫声,那头生物掉进了陷阱里。汉亮飞奔上前,将邻近的小树砍倒,倒下来的树冠枝叶正好压在坍塌口。公鹿无论如何也不能出来了。汉亮又砍下些别的树枝,把能射过阳光的问隙盖住,以免坑内温度升高。然后砍了些嫩枝叶塞进坑内,一路飞奔下山。
黑松林营地的小木屋里,王明福一边端着砂锅往碗里倒煮好的人参汤,一边哼着当时流行的歌曲“敬祝你,老人家,万寿无疆”。
他长长地吮饮了一口人参汤。“啊,万寿无疆不要,长寿不老就可以了。”
“明福,”正进门来的刘颐圳朝他大喝一声,吓得明福烫着了自己的手,“你又喝人参汤啦,你倒好,种啥吃啥。”
“大刘你轻点,你不尝蜂蜜啊?你养的蜜蜂到我种的人参花上采蜜,然后,你喝了那人参花蜜,不也是长寿不老嘛。”
这时木屋里的那架老式摇把子电话的铃声响了。明福拎起话筒。
“喂喂,哪里啊,队部?……听不清,什么打炮……又要修路啦?……什么?下雨?……我们这里没下雨。鹿?……鹿又怎么啦……听不清……喂喂……”
明福无可奈何地一摊手。“你看又断线了。”刘颐圳接过电话,使劲地摇那把手。电话机里除了嗡嗡声,再也没有别的声音。“……谁的电话?到底说了什么?”
“听不清,什么打炮下雨,鹿,像是连部文书张勤的声音。……哦,汉亮回来了。有没有鹿的好消息。”
“窖到了头大公鹿,很大的茸角。”汉亮满面流汗地放下背囊。
“难怪连部打电话来讲到鹿,八成是要嘉奖你。”
“他们不会知道,我刚从山里下来。”
“别听明福瞎扯!汉亮,大公鹿更难圈养啊。你看,我们窖到它了,拉了回来,几天后它在圈里自己撞死了,这种做法有问题……”大刘说道。
“死了吃鹿肉!”明福高兴地在一旁叫道。
在金黄色的夕阳余晖下,三个年轻人都帮着老杨头修缮鹿圈舍。快完工时,老杨头吩咐道:“用牛皮条把栅栏门绑好,就歇工了。我去准备车马器具,明天一早我们四个都出车,把那只窖到的鹿拉回来。”
在大山西侧的一个山坳里,新的高炮阵地设立起来。暮色苍茫中,六门高炮指向天空,每门炮的周围还清出一大块场地。因为退膛的弹壳仍带高温,很容易将枯枝干草点着,引发森林火灾,特别是今年干旱。他们对场地清理格外仔细。
邓团长在各炮位四周严格地督查。炮阵地的一侧支起了几个野营帐篷,准备在这过夜。离炮阵地稍远的高坡上,一块大油布系绑在几根树干上,遮住一片天。油布下大略平整过的地面上安置着一台大收发报机和一些仪器设备。
油布篷下韩琳珊独自一人坐在收发报机前,大耳机套在她浓发的两侧,她专心致志地收取气象数据。油布篷的四周没有遮拦,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山林显得幽暗。炮阵地上传来的嘈杂声掺和着群山的回荡,似乎从时空的那头飘来,隔着几个世纪,显得陌生。
夕阳只显现在远处的山峰顶上,从林隙间返射的天光,映出琳珊聚精会神的身影,她的脸庞是那样的白皙,如大理石雕就,含有温润的玉的质感,显出古典的韵姿。
她摘下耳机,无意中往山林深处一瞥。突然,她惊讶了,瞬间又凝固住,那神情既古典又现代。她看到了一只狼,一只大大的灰狼。狼的额头和两只高耸的耳朵是黑色的,长长的嘴是白色的,鼻子顶端则是黑色的。脖子下是柔软蓬松的白色的毛,下沿是一圈黑色的毛。全身则是黑白掺杂,呈灰白色。那只狼无声无息地注视着她。
韩琳珊惊跳起来,没有出声,跑到空地上,显得极度惊慌失措。差点儿跌倒,转了几个圈,看到不远处人们都在忙碌,没有一个人注意她。
她犹豫着回到布棚里,朝那里望去。除了远处阳光下斑驳的山林,近处摇曳的枝叶,没有狼,没有其他动物。她怀疑自己看花了眼,又坐下来。静等许久,树林里仍没有任何变化。她才带上耳机重新工作。但不放心地又朝仪器背后望去。那只狼,还是那只狼,蹲坐在那里,无声无息地注视着她。毛发蓬松,白中掺黑,那样的近,就在布棚外侧。
琳珊此时沉不住气了,扔下耳机,狂逃出去。
“啊……一只狼,一只大灰狼!”
她惊叫道,声调颤抖,充满着恐惧和惊惶,拽住陈原的臂膀,躲到他身后。陈原见状,放下手中的测风仪,操起炮车上的一支步枪。“在哪里?哪里?……啊,真是一只狼。”他举枪瞄准,正要射击。不防琳珊推起他的枪。“呼!”子弹射向天空。
“不要开枪,我不要你伤了它。”琳珊嘶哑地叫道。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垂下头,显得相当忧郁。
炮兵们都奔跑过来,那只狼蹦跳几下,消失在树林里。
“发生了什么事?”邓团长严厉地问。
“一只狼,就在琳珊的布棚边上。”
“狼?不就是比狗凶点吗?用不着大惊小怪的。”邓团长仍然没缓和口气,又补充地朝大伙喊:“没有我的许可,任何人不可动用枪。”
“惊着你吗?琳珊!”邓团长扶起弯着腰的琳珊,问道。
“还好,”琳珊勉强一笑,“我觉得它倒没有凶相。”
“山里狼多,遇到是平常事。”
“奇怪,团长,这不是一只平常的狼,”陈原若有所思地说,“它不是本地东北狼,也不是西伯利亚狼……好像是一只阿拉斯加的灰狼。”陈原肯定地说。
在渐黑的夜色中,谁也没有注意到,琳珊打了一个寒战,双目中流露出更多的惶恐。
天色尚未放亮,老杨头就把三个小伙子叫醒,一起上路了。一匹单马挂着一辆小马车,由汉亮牵着在崎岖的山路上辘辘而行。其余三人跟在车后,明福不时地拉住马车梆,让马车拖着他走。浓云密布的山梁上空,尚不见日头的行踪,他们一行已赶到了六道横子的窖坑。
那只被窖住的鹿听到人的声响,在坑内使劲地撞四壁。老杨头叫人移开树枝,从一个空隙处扔下带套的绳索。只见他甩动几下,绳索就已经扣住了一对大茸。老杨头把绳索的另一端往近旁一棵大树的枝杈上一抛,然后抓住绳索垂下的那一端,慢慢地抽紧。那窖内的鹿头就被吊挂了起来,前肢也离开了地面。但鹿仍然用后肢蹦跶。老杨头又甩进去一根绳索,套住了它的后肢,用力一拉,那鹿便侧倒在窖坑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