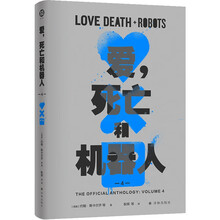五段楔子全交代过了。
请大家注意,在这五段楔子中出现过的主要人物,以出场的次序计,总共有:
我──卫斯理,不必多介绍。
神秘的黑衣长发女郎──和我讨论过一幅题名为“茫点”的画,但是自始至终,未曾见到她的模样。
杀手──一个职业杀手。
杀手的委托人──一个和杀手作了对话之后,终于委托了杀手去杀人的人,身分不明。
桃丽──金发碧眼的标准美女,性子活泼好动。
葛陵──军衔是少校,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美国太空人。
安普女伯爵──富有,虽然已届中年,但仍然十分动人。充满了成熟女性魅力的欧洲社交场合中的名人。
陈岛──中奥混血儿,生物学家,固执地相信自己的理论,埋头研究蛾类互相之间的沟通方法。
尾杉三郎──日本的九段棋士,在棋坛上,有“鬼才”之称的高手。
时造旨人──一个未成名的小说家,替一些杂志写些零碎的稿件。
这些人,在每一个楔子之中,都发生关连,但是在不同的楔子中,一点关连也没有。
这些人,能组成一个甚么故事呢?
我是所有故事的当然主角,所以,故事由我开始。
那天,白素不知道有甚么事出去了,我选了一张爵士鼓唱片,将音量扭得十分大,让咚咚的鼓声,将我整个人包住。
鼓声震屋,突然我肩头上被人拍了一下,回过头来,看到白素已回来,她皱著眉,正在向我说话,我忙按下摇控声量的掣钮,鼓声消失,才听到白素的声音:“你看你,客人在门口按铃,按了二十分钟,你也听不到!”
我这才注意到,门口站著一个男人,那人穿著一件浅灰色的雨衣,雨衣上很湿,我连外面在下雨也不知道。我站了起来:“我好像并没有和这位先生约定过,他是──”
那男人在我望向他的时候,他正转身在脱去他身上的雨衣,所以我没看到他的脸。
等我讲完这句话之后,他也脱下了雨衣,转过了身来。
那是一个年轻人,对我来说,完全陌生,他大约二十七八岁,相貌相当英俊,一副惶急神情。
我看到是一个陌生人,不禁瞪了白素一眼,有点怪她多事。如果我听到门铃声,去开门,看到是一个陌生人,决不会让他进来烦我,在门口就把他打发走了。
白素压低了声音:“这位先生正需要帮助!”
我不禁苦笑,这时,那个年轻人已经向前走来,神情仍然惶急,搓著手:“卫先生,卫夫人,真是冒味之极,我……如果在其他地方,有办法可想,决不会来麻烦两位。”
我听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是啊,我这里包医疑难杂症。”
那年轻人被我一抢白,满面通红,他不是很老练,在那霎时间,他不知道如何应付。白素十分不满意地瞪著我。我心想,我管的闲事也太多了,甚么事情,都要我去寻根究底,让白素去理理也好,反正已经有不少人认为,她比我能干理智。所以,我让白素去处理这宗“疑难杂症”。
我向白素调皮地眨了眨眼,我们之间已经可以不必说话,就互相知道对方的心意,白素也立时扬了扬眉,表示“我来就我来。”
我笑了一下,心中在想:别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那年轻人可能说出不知甚么样的稀奇古怪的事来,到时,看你怎么应付!
我一面想著,一面已转过身去,可是就在那时候,那年轻人已经镇定了些:“我哥哥告诉我,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想,可以来找卫……先生,卫夫人,他也叮嘱过我,不到万一的时候,别去麻烦人家。”
我走向楼梯,听到白素在问:“令兄是谁?”
那年轻人道:“哦,我忘记了介绍我自己,我姓张,单名强,我哥哥叫张坚,一向在南极工作。”
我已经踏上了两极楼梯,一听得这两句话,我不禁呆住了。
那年轻的不速之客,原来是张坚的弟弟!真该死──他为甚么不一进来就讲明自己是甚么人呢?如果他一上来就说他是张坚的弟弟,那当然大不相同,我也绝不会给他难堪。
张坚是我的老朋友,我和他在一起,有过极其奇妙的经历(《地心烘炉》),他是一个著名的南极探险家,有极其突出的成就。
更令人可敬的是,张坚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极其有趣、值得崇敬的人!虽然他的弟弟,可能十分乏味、无趣,但是既然是张坚的弟弟,有事找上门来,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我一想到这里,已经准备转过身来了。
可是就在这时,我却听到了白素的声音:“哦,原来是张先生,令兄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好吗?卫先生是最近事情很忙,你有甚么事,对我说,完全一样!”
白素在说到最后一句时,声音提得特别高。就算感觉不灵敏,也可以听出来,她说“完全一样”这句话的意思,是找她比找我更好。
这令我感到非常无趣,不过,来人既然是张坚的弟弟,问候一下张坚的近况,总是应该的。
所以,我在楼梯上转过头来:“原来你是张坚的弟弟,张坚好吗?”
那年轻人──张强──看来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我哥哥?他很好,在南极。”
我心中暗骂了一声“废话”,张坚不在南极,难道会在赤道?
我又问了一句:“要和他联络,用甚么方法?”
张强这一次,倒答得具体一点:“通过纽西兰的南极科学探测所,可以找到他,他们会转驳电话到南极去,最近才有的!”
我“嗯”地一声:“是啊,利用人造卫星,我应该和他联络一下。”
我故意找话说,是希望张强会想到,他是张坚的弟弟,我一定肯帮他的。只要他再一开口,求我一下,那我就可以下楼了。
可是张强这小伙子,却木得可以,一点也不通人情世故,竟然不作第二次恳求,而白素则显然看透了我的心意,似笑非笑地望著我。我瞪了她一眼,继续向楼梯上走去。
我把脚步放慢了一些,听得白素在问:“究竟有甚么问题?”
张强答道:“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卫夫人……”
白素挥了一下手:“叫我白素好了。”
张强道:“这……这种事很……怪,唉……我从十天前开始,唉……”
张强这个人,婆妈得令人讨厌,究竟有甚么问题,爽爽快快讲出来,我也可以听得到,可是他却偏偏支支吾吾,却语还休,我总不能老赖在楼梯上不上去!
我心中骂了张强两句,赌气不再去听他讲,加快脚步,到了书房中,在书桌前坐了下来,顺手拿起电话,拨了纽西兰的电话,问到了那个探测所的电话,再打过去,要他们转接在南极的张坚。等了约莫二十分钟,才有人接听,我说要找张坚,那边的回答是:“哦,你找张博士,真对不起,他现在不能接听电话。”
我有点恼怒,道:“叫他来听,不管他在干甚么。”
那边的回答令我啼笑皆非:“张博士和他的助手,驾著一艘小型潜艇,在二十公尺厚的冰层下航行,和外界完全断绝联络,真抱歉,无法请他来听你的电话。”我无法可想,只好放下电话,生了一回闷气,听到下面有关门开门的声音,我想是张强走了。张强如果走了,白素该上来找我了。
我等了一会,白素还没有上来。我等得十分不耐烦,打开书房门,叫了两声,没有回答。我不禁伸手在自己头上打了一下,真笨,为甚么只想到张强走了,而没有想到白素和张强一起走。
我下了楼,果然,楼下并没有人。张强不知道对白素说了些甚么,白素一定去帮他解决困难。这本来也算不了甚么,白素和我,一直都热心帮别人的忙。
可是我却看到,客厅的一角,有几件不应该有的东西在。
那一角,有一组相当舒服的沙发,如果客人不是太多,只是一两个的话,就经常在那个角落坐著谈话,刚才白素和张强,也在那里交谈。
一组沙发中间,是一张八角形的茶几,我所指的不应该有的东西,就是在那茶几上。
所谓“不应该有的东西”,绝不是甚么怪异的物品,东西本身极普通,只是不应该出现茶几上:那是几面镜子!
我走近去,发现一共是四面,其中一面相当大,长方形,一面是圆镜,还有一面,十分小,是女人放在皮包中的小方镜子,还有一面,镶在一只打开了的粉盒盖上。
那只粉盒,白色法郎质,嫩绿色小花,十分雅致,我一看就可以认得出,那是白素惯用的东西。这时,粉盒打开著,显然,曾经用过盒盖上镶著的镜子。
看看这四面镜子,我不禁有点发怔,这算是甚么名堂?那三面镜子,不是我家里的东西,一定是张强带来的,他在门口脱那件雨衣的时候,我就曾注意到他雨衣的袋子很重,像是放著东西。不过,就算那时叫我猜,我也猜不中那是三面镜子。男人随身带著三面镜子,太怪异了!
从留在茶几上的镜子看来,张强和白素的对话,一定和镜子有关,不然,白素的粉盒不会在几上。略为推理一下,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强的话题,和镜子有关,他一面说,一面拿出他随身带著的三面镜子。而白素有点不信,也拿出了她身边的镜子。
我自信,经过的情形,大抵是这样的。可是,镜子有甚么值得研究呢?
我一面想,一面拿起镜子来,看著。那只是普通的镜子。在我对镜子看的时候,镜中反映出我,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
我把四面镜子全拿起来照了照,结果自然一样,我对著镜子在照,镜子中出现的,一定是我,不会有甚么意料之外的变化。
我心中十分纳闷,放下镜子,我想在白素回来之前,把答案找到。可是我怔怔的想了好久,从各方面去推测,都想不出所以然。
心中有疑问,是十分闷气的事,等了一小时,好像十小时那么久,楼上楼下跑了好多次,白素连电话都没有打来。
好不容易,书房的电话响了,我冲上楼去,拿起电话,以为一定是白素打来的,可是电话一拿起来之后,那边传来的,却并不是白素的声音,而是一个听来极为兴奋的声音:“卫斯理,你快来,立刻就来,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给你看。”
声音,肯定是熟人,但是一时之间,却想不起那是甚么人来。
我只好道:“请先告诉我尊驾是谁,我该到甚么地方来看那意想不到的东西?”
电话那边那个人叫了起来:“天,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
我“哼”了一声:“是,我最近耳朵犯聋。”
那边停了一停:“是我──”他在讲了两个字之后,忽然拉长了语调:“恨君不似──”
他才吟了四个字,我就想起是甚么人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南北东西,我不相信你会有甚么意外给我!”
那人“哈哈”大笑。“南北东西”当然不是那个人的名字,只不过熟朋友都这样叫他,因为他的名字叫江楼月。宋词中一首“采桑子”,第一句就是“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所以,这位江先生的绰号,就叫“南北东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