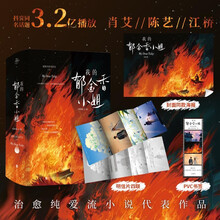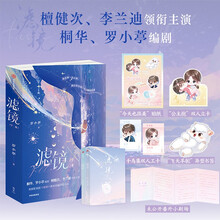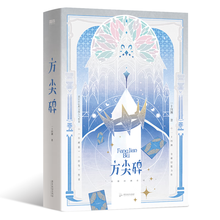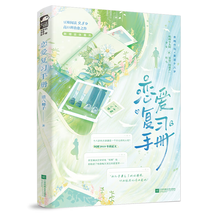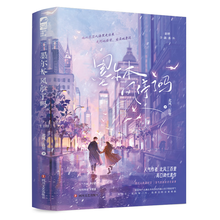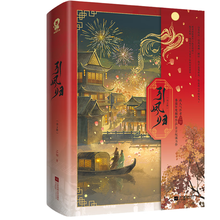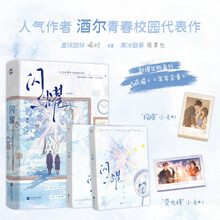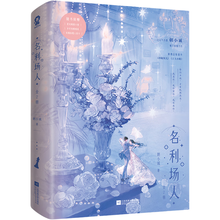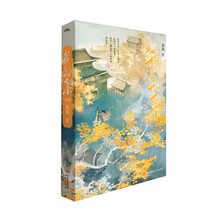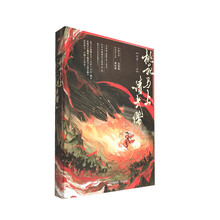第一章 长安京<br> 冬日,延英殿。<br> 内侍少监徐常礼指挥中人们取下元宵节的宫灯,扫去庭前的积雪,寒风刺骨,大家虽然穿着厚厚的棉衣,仍是冷得不停哆嗦。<br> 忽然听到皇帝传唤,徐少监赶紧入内,瞥见皇帝脸色有些微不寻常的红,连忙使眼色给一旁的小康福,叫他减炭。<br> 皇帝抬头问道:“今夜值宿的是哪位大臣?”<br> “回皇上,是中书侍郎袁思泰。”<br> 皇帝皱皱眉,摔下手中的奏折站起来,缓步走到窗边,望着天上的雪花出神。<br> 今上不喜召见国舅爷,这已是内侍们摸清的规律了。皇上幼年丧母,由袁皇后抚养长大,母子之间一向有点怪怪的,袁大人倒是国舅的架子摆个十足,朝中很多大臣都是他提拔的,皇上有什么决议,他们总会诸多掣肘。外头几个藩镇的节度使又爱自说自话,这龙椅啥时候才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呢?<br> 皇上本想趁今年科举,真正选几个称心的人帮自己,哪知道一干大臣都纷纷进表,说什么“请以袁侍郎知贡举”。惹得他老大不高兴。<br> 不过他还是很体贴地问了各州举子是否到齐了,还派尚衣局查访待考诸生是否缺少冬衣。<br> 考生到得七七八八,考官却还没定下来。<br> 徐常礼看时辰不早,传令关闭延英门。皇帝回到桌旁,默想了一会儿,挥毫写下“正安”两字。康福在一旁研墨,大喜问道:“陛下已经想好新的年号了!?”<br> 皇帝左右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字,真是无一处不满意:“可惜萧澈他们被我赶回家了,否则看了这两个字还不输得心服口服?”<br> 康福笑嘻嘻地说:“萧侍卫一回府就被太师关了起来,一个月都没出门。”<br> 皇帝亦含笑点头:“可怜澧泉坊、平康坊的姑娘们只怕要哭得泪眼昏花。”<br> 同一时间,一队士兵护卫着几十辆马车从金光门入城,其中四五辆载着今春应考的士子,被安顿在布政坊清平舍馆。其余车上盖着厚厚的布,上书“陇右道肃州酒泉郡贡”,一看便知是给朝廷的贡品,继续往大明宫驶去。<br> 舍馆小二忍不住嘟囔:“累了一整天,睡觉都不得安生,官府就只给我们那一丁点儿钱。”<br> 老板把抹布用力甩到他脸上骂道:“傻子,咱们店里住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说不定哪天就当宰相了,到时小心你的皮!”<br> 老板虽没读过书,也曾听醉仙楼的说书人讲,皇帝选大官要看“体貌丰伟”,就是人要长得壮,还不能太丑。这批肃州的人倒还能看,就是其中有一个瘦不啦叽的,面有菜色,穿得那么差还外带个病恹恹的书童,是以这位崔小哥问他讨点药时,他很不屑地不予理睬。<br> 翌日,那书童似乎病得更重,崔小哥跑出去请大夫、买药,回来时老板大吃一惊——他竟然把官府送的棉衣当掉了。老板感叹,到底是外头来的,不知道规矩,皇帝给的东西是你说不要就不要的吗?<br> 之后几天,崔小哥天天一早出去,晚上才回来,书童的药倒是交代厨房按时煎好。老板起了疑心,假装送点心过去,远远看见一个士子在敲崔小哥的门喊着:“敏直,敏直!”显然是想借棉衣给他。不一会儿士子就觍着脸出来,棉衣还是没有送出去。<br> 后来老板偷听到崔小哥对书童说,宫里最近急召“御书手”,就是帮皇宫藏书阁抄书的,他抄得快,一天能挣五文钱云云。<br> 崔敏直哪知道隔墙有耳,每日仍在明德殿埋头抄书。中午宫里管一顿饭,外加两款糕点,日日不同花样,他就偷偷留着带回去给篆儿。校书郎见他抄得勤快,涂改又少,字也是难得的端庄秀丽,乐得把自己名下那些古旧生涩的破书也指派给他。<br> 午饭时间,御书手们最爱交头接耳交流一下宫里的秘事传说。这明德殿很多年前差点被一场大火烧个精光,先帝降旨说既是意外,不必查究是谁的过错。大伙儿明里不敢议论,暗里总免不了胡乱猜测一通。<br> 崔敏直正听得津津有味,校书郎突然进来唤他出去。出了明德门,两三个面熟得很的肃州士兵就按住他,从袖里搜出应考名牒来。校书郎顿时黑了脸:“崔小郎官,陛下给了天大的恩典,让各州府派车送你们上京赶考,一路好吃好住,你总得用心准备考试才是,怎么跑到我这里胡闹,辜负陛下的美意!”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