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937-1942年的“鲁迅”
第一节 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
在整风运动以前的延安,鲁迅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身份就受到了尊崇。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10月22日张闻天就代表中国共产党起草了三份文件:《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书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电》。这三份文件代表了共产党中央从政治战略的角度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作为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张闻天较为重视鲁迅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他充分认识到了鲁迅在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的影响力:他在文件中称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说鲁迅的逝世,使得“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这也是鲁迅逝世后各进步报纸对鲁迅的基本评价。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创立时,发起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也一致认为鲁迅是“中国最大的文豪”。
从1937年至1940年,在延安尊崇鲁迅的氛围中,鲁迅的文学贡献被一致肯定,只是有关的言说与“研究”无关。而且这些言说有很多雷同之处,更像是在复制政治领导人对鲁迅的阐释并相互复制。这大概是由于这段时间延安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抗战救亡,那里常有战事,知识者无暇精心研究鲁迅的著作。陈伯达认为“鲁迅是我们民族近代最伟大的文豪”。艾思奇称鲁迅为“中国新文学运动最优秀的产儿”。萧三认为鲁迅是中国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创立者、鼻祖。萧三和周扬都谈到鲁迅从事文艺的动机在于改变民族和国人的精神——有关鲁迅的评论仅止于此。1938年鲁迅逝世二周年时,成仿吾、周扬、艾思奇纷纷著文表达他们对鲁迅的认识与怀念。成仿吾在《纪念鲁迅》一文中认为鲁迅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黑暗,民众的悲哀,没有希望”,鲁迅“创造了一种新的小品文,用了最尖锐的笔锋,打击了当时的背叛、虚伪与黑暗”。周扬在《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中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肯定鲁迅的作品,认为它们“是中国新文艺最初的也是最丰富的收获,是中国新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的第一块坚固的基石”。艾思奇在《学习鲁迅主义》中认为“鲁迅的作品是热情的,然而不是浮泛空洞的叫嚣;他的作品是现实的,然而不是观照的,离开斗争立场的素描的写实。他坚决地摧毁了中国的一切陈旧的文学传统,然而并没有忘记仔细地在废墟里找出应该发扬的好东西”。至于鲁迅究竟摧毁的是哪些文学传统,发扬的又是哪些好的传统,艾思奇并没有说明。他为了强调鲁迅的“立场”,将“现实”即写实与“观照”对立了起来。在延安的战时氛围中,鲁迅作品的认识价值得到了重视。如萧三认为“中国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一切事变,人物与现象,在他(鲁迅)的丰富作品里都看得见,都得到正确的、不歪曲的反映,这是一部绝妙的历史文件。研究中国现代历史者非读鲁迅的杂感不可”。陈伯达认为通过鲁迅的著作可以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历史和现代中国的各方面的面目”。在普遍的模式化的赞美中,荒煤阅读鲁迅作品的个人体验就显得较为特别了。荒煤,原名陈光美,湖北襄阳人。1930年代,他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活动,后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开始小说创作。1938年秋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荒煤在文章中说“很偶然地我得到了一本《南腔北调集》,我又偶然地首先读到了那一篇纪念柔石及其他几个遇难的青年的文字,我深深地感动了。我记得在那天晚上,一个黑黝黝的夜里,我独自坐在咆哮的海的身边,心扉激动地开翕,我感到我在黑暗的世界里嗅到了一股强烈的血腥气”。荒煤在文中说每次读完《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都会“觉得心是颤动的,沉重的,连呼吸都窒息起来”。荒煤的个人阅读不负担特殊的政治和历史认识的功能。用钱理群的话来说,是一个生命个体和鲁迅的个体生命的相遇或对撞。
1939年延安“民族形式”论争中的“鲁迅”变得丰富起来。对“民族形式”的来源持不同意见的双方普遍认为鲁迅的作品是民族形式的典范。认为旧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主要来源的艾思奇认为,“他(鲁迅)的作品所以成为‘五四’新文艺运动的最高的成果,也正因为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但是新的,而且也是民族的”。萧三在谈到诗歌的民族形式应该较多地利用旧形式时,用鲁迅创作旧体诗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你只要读一读他(鲁迅)的发表得不多的旧诗,你只要去读一读他伤悼柔石、殷夫几个青年作家惨死的诗,你会要大大地深深地感动,你会想到柳亚子先生评鲁迅先生的诗所说的‘郁怒情深,兼而有之’这句话及其正确。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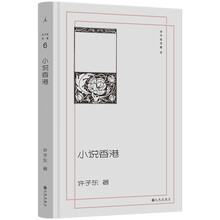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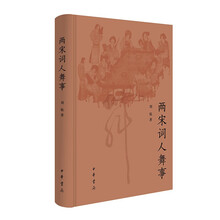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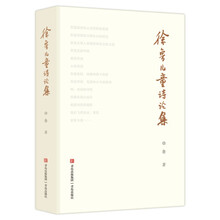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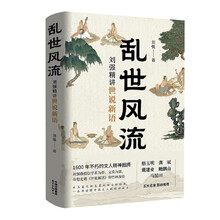
——孙郁(鲁迅博物馆馆长)
《“鲁迅”在延安》着重梳理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斛读鲁迅的独特方式,意在把握“鲁迅”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延安是如何展开的,鲁迅是如何被叙述、被言说的,进而揭示当时延安精神空气的特点及其衍变,以及延安思想文化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复杂纠葛,应该说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学术工作。《“鲁迅”在延安》这一题目要求回到“历史现场”,这就需要查阅大量原始资料,作者在这一一方面是下了功夫的,而且还阅读并诠释了一些过去不大为人们所知的第一手材料,尽可能地做到了“用史料说话”,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王培元(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