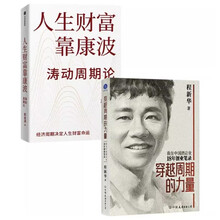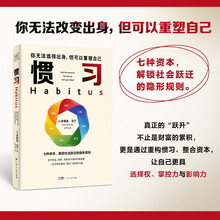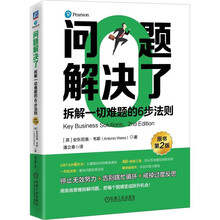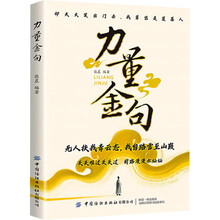天鹅湖畔的爱
我的孪生姐姐叫思芭,我叫思蕾,妈妈给我们起名的时候,梦想我们能成为玛格·芳婷、乌兰诺娃那样耀眼的芭蕾舞巨星。事实证明了思芭和我在舞蹈上显现的天赋,小时候,还站立不稳的我们,就学着大人的样子,踮着脚尖在床上跳啊跳的。6岁那年,我俩一块儿成了舞校的学生。
我俩最喜欢排练的剧目是《天鹅湖》,最喜欢的角色自然是公主。思芭和我是奥吉塔公主的当然入选。但是一出剧中只能有一个公主,于是,我们中的一个必须放弃,去扮演魔王的女儿奥吉莉亚。奥吉莉亚虽然和公主长得极为相似,却有一副恶毒的心肠,千方百计要夺去公主的心上人。每次我不得不饰演奥吉莉亚的时候,总是委屈地哭红了眼睛,这成了我俩深深的遗憾。
16岁时,我和思芭分开了。她去英国皇家舞蹈学院深造,我则开始在国内的舞台上崭露头角。20岁那年,我攀上了个人艺术的巅峰,主演的《天鹅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我收到思芭在网上发来的照片,那是她的一张舞台剧照。照片上的“天鹅”美得令人窒息。略过时差不计,思芭和我在同一天实现了人生的梦想,我们都成了当之无愧的“公主”。
那之后,我退出了舞台,娱乐周刊上说我急流勇退,我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超越我的巅峰,我的记忆定格在谢幕前的那一刻:恶魔被铲除了,天鹅们全都变回了少女,包括我——奥吉塔公主在内,我和我的王子齐格弗里德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半年来,我避开所有的记者,蛰伏在僻静的蜗居中潜心写作。
在一次归国探亲的飞机上,思芭和俊文一见钟情。思芭给我看过他的照片,照片上的大男孩英俊帅气,还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不知为什么,我仿佛看见了齐格弗里德,那个我梦境中的王子。也许就在那个时刻,我有了一个恶劣的病症——在电脑上码字儿时我总是偷偷地用思芭的QQ上线。思芭的密码我用不着破译,因为我俩的密码只有一个,因为她的生日也是我的。俊文在思芭的好友名单里,看着他的头像不住地晃动,我忍不住打开了对话框。
就像吸食了鸦片般难以克制,我在QQ上用思芭的身份和俊文交往了半年,而他浑然不觉。我和思芭有着怎样的默契啊,我的思想,我的灵魂,无一不是思芭的影子。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会突然惊醒,发觉枕头湿湿的,浸着我的泪水。
思芭若是知道我在盗窃她的爱情,她会怎样呢?
俊文就在这个城市上班,我清楚地知道他的写字楼和我住的地方只隔两条大街。我在对他的爱和自责中煎熬,我几乎想象过代替思芭的出现,我和思芭长得太像了,没有人能分辨出来。思芭告诉过他我的一切,包括我的那场汇演。我好想在QQ上捕捉到俊文对我的印象,可是他从来不曾提起过我,他眼中只有思芭——另一只迷人的“天鹅”。我好想对他说,虽然他没有白马,却是我的王子。
晚上梦见思芭了,梦中,她是那只被魔王下了诅咒的天鹅——奥吉塔公主;而我,却成了我最讨厌的角色奥吉莉亚,假冒公主去引诱王子……从梦中哭醒时,我在心里做出了决定。俊文的出现不是错,错的是在我以为我和思芭都是公主的时候,王子只有一个。我最后一次上了思芭的OO,敲下“保重”两个字,便退出了。
思芭回来了,我跑去接机。见到思芭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俊文和她一起向我走来。他的相片我看了千遍万遍,远远的,人群中我也能一眼认出来。我忽然觉得无地自容,俊文早在两个月前就到海外公干,一直陪在思芭的身边。
俊文眼里有一丝关切的神色,对我轻轻地说了声“保重”。
思芭似乎没有觉察,笑嘻嘻地挽着他,又热情地挽住了我,我们三人一起朝出口走去。
我明白:俊文知道,思芭也知道。
搪瓷白缸
一向身体健朗的他生病了,老年痴呆,来势汹汹,雪崩山倒之势。先是不认识回家的路,辨不清两个女儿,随后记不得自己的名字,再后来发展到不得不住院治疗。
住院的他,每天除了打针沉睡之时平静一会儿,其他时间像个小孩子不得安生,拍手吵闹不停。最让女儿头疼的是吃饭,饭菜吃得漓漓落落的,还会被他打翻弄得床单衣服上到处都是。一顿饭吃下来,喂他的女儿累得满头大汗。
那天,女儿手忙脚乱打碎了保温瓶,匆忙中只好从柜里随手拿出一个搪瓷白缸,将饭菜盛好送到医院去。也许是因为有他爱吃的红烧鱼和香菇碎肉,他吃得特别香,而且出人意料地吃得很安静,直到把饭菜吃个底朝天。女儿惊讶得不得了,以为他的病情开始好转。临吃完,他望着准备走的女儿说:“你回去告诉淑贤,我很好,别让她担心,我很快就回去。”女儿微笑地回答着“好。”心底却深深地叹息,父亲越来越糊涂了。淑贤是母亲的名字,她已经离开他们许多年了。
那段日子,他变得安详起来,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很合作,像个不再惹事的孩子。女儿不再为他吃饭犯愁。可每次当女儿离开时,他都要让她给淑贤捎话,不外是让她不要担心,他很快就会回家。有一天,他趴在窗台上喊住已下楼的女儿,说:“天冷了,让淑贤多穿衣服,她身子弱!”
天气真的越来越冷了,搪瓷白缸带的饭菜送到医院已没有了热气,女儿又买来一个保温瓶。没有想到的是,热乎乎的饭菜放在他面前,他却旧态复发,不肯轻易吃下一口,任凭女儿千说万哄。最后气得女儿喊道:你怎么可以这样气人?是不是看碟下菜?话一出口,女儿怔住了,忽然想起了什么!
回到家,搪瓷白缸静静地立在桌子上,在灯光下泛着年代久远的光泽,那是母亲曾经用过的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