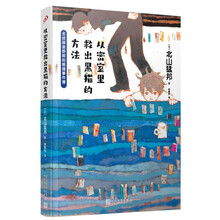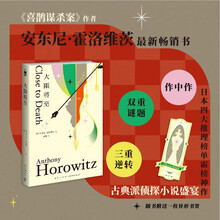让我感到非常不自在的是,整个晚上,里德夫人的位置不是紧靠在她那幅新画像的左边或右边,就是站在画像的下方。为了出席今天的这个场合,她穿着黑色礼服、戴着钻石项链,和那天摆好姿势让我画像时我要求的穿戴一模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上帝之作和我的作品做一比较势不可免。我敢说,万能上帝的原作,在这幅经过我绘画艺术修正后的作品面前,似乎有些缺憾。然而,上帝以他那无可置疑的智慧,认为里德夫人的鼻子应该是宏大的,在她的两颗门牙之间留有明显的空隙也很合适。我将门牙排列得整齐合缝,把那些使她与别人得以区分的特征调整到正常的美观状态。通过运用一丝淡淡的玫瑰色、尽量不用明暗对比法,为整幅画的色调增添了某种年轻的神采弈弈,她的肉身也充满了弹性。如果将时光的闹钟只回转几分钟,那么我做的这些相应的调整就显得多余,变得非常好笑了。<br> 或许里德夫人对画像和自己之间的差异全然不知,但也许她知道这一切,只是她认为如果尽可能站得靠近自己漂亮的复制品,她将使朋友和家人的心中分不清谁是艺术品,谁是真人。或许她在心里盼望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完成肉身和油画之间的转换,就像王尔德最近的小说《道林·格雷画像》之中的情节一样。无论此时属于哪一种情况,里德夫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至于我们这些在场的人,故意对真实视而不见让我们感到很不自在,因为我们都是“同谋”。谢天谢地,她丈夫花了一小笔钱买了上好的香槟,让所有人开怀畅饮以此庆祝画像的揭幕。<br> 到场的五十多位客人觉得有必要走过来,对我的作品美言几句,然而,要不是因为酒精的作用,对于这部作品,我的面部表情应该永远处于皱眉蹙额的状态。<br> “皮安波,里德夫人身边桌子上鱼缸里的金鱼你画得太棒了!鱼身上的每片鱼鳞都能数得出来!”<br> “她身后那只中国花瓶上永不凋谢的金莲花就像真的一样。”<br> “你画的礼服上的皱褶手法之高超,无人能及,啊呀,我的天,你看那些钻石在闪闪发光呢!”<br> 我不失礼节地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为里德夫人所做的事情,将来也会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身上重演。我想自己终于可以独自待着安静一会儿了,这时我那画像艺术界的同好——舍恩兹悄悄踅到我身边。这小个子神气活现地留着修剪得恰到好处、末端尖尖的络腮胡须,因为坚持拉斐尔前派的理念,还为范德比家族一些名声不太响的成员画过肖像而出名。他站在宽敞客厅的一头盯着里德夫人的肖像,嘴里衔着的大雪茄后面藏着一脸的坏笑。<br> “皮安波,你画得不错。”他说道,然后微微转了一下头,调整视线看着我。<br> “你再多喝点香槟吧。”我低声对他说,他无声地笑了。<br> “对这幅画,我觉得用‘有益身心’这个词形容很合适。”他说,“对,十分有益身心。”<br> “我不断在心里记着账呢。”我告诉他,“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表扬金鱼的人多,还是表扬金莲花的人多。”<br> “那你把我记在表扬鼻子的人那边。”他说。“油彩用得极俭省,不愧是大师啊!”<br> “我觉得那也是里德最喜欢的一点。他为了这幅画出价不菲呢。”<br> “噢,那他是应该的。”舍恩兹说。“我觉得你这神奇的画笔让他的妻子彻底忘记了他和梅西百货公司那位年轻售货员之间的行为不检。如果不考虑他那间制鞋工厂新近滚滚而出的钞票,我们可以说,只有你的绘画技能才可挽救他的婚姻和尊严。”<br> “主知道世上还有比绘画更重要的东西。”我说。“谁是你的下一个受害对象?”<br> “今天晚上我刚刚受托给豪奇特尔家族肥头大耳的子孙画像,好让他们流芳百世。这两个脑满肠肥的小怪物,我正考虑是不是要给他们喝点鸦片酒,好让他们在画像的时候给我端坐着不动。”离开之前,他举起香槟酒杯,表示祝贺。“为艺术干杯。”说着,我们俩手中精致的水晶酒杯碰在了一起。<br> 舍恩兹走后,我在客厅角落里的一盆蕨类植物旁边找了个座位,点燃了一支雪茄,升腾而起的烟雾形成了一道供我躲避的屏障。此时的我已经喝了太多的香槟,感觉有些头重脚轻。客厅正中那装饰华丽的枝形吊灯反射的光线,再加上纽约社交界这些新贵们的妻子身上的珠光闪烁,让我几近丧失视力。聚成一团的客人发出的嗡嗡的声音,偶尔也有一两句对话飞到我耳朵里,所以几分钟后我就听明白了,原来他们在讨论什么芝加哥的哥伦布展览会啦,《纽约世界报》刊登的新卡通画《沿着霍根小巷》中那个身穿男式衬衫做睡衣的男孩儿的最新滑稽动作。<br> 两天后的下午,我沿着沙滩漫步。我无法集中心思工作,而且卢米斯神父今天也外出了。我走到海边的沙滩,坐在我经常坐的那堆浮木上。远方地平线处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空气变得干冷,海湾里的海水几乎都要结冰。我吸了一支烟,想着纽约这座城市。此时我才发现我一直在思念着它。白天的光亮没有几分钟就要被黑暗吞没,我站起身准备回画室,此时看见远处有一个人,沿着海岸慢慢向我靠近。第一眼看去,那人好像长着天使般白色的翅膀。那双翅膀在最后的阳光中发疯般扑腾着,闪耀着。一股恐惧感通过了我的全身。说不定那是露西埃尔的鬼魂回来向我讨回那枚吊坠。后来我终于看清,那双翅膀原来是一条白色披肩的两端,这时我也认出了那个人。我迎面向她走去。<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