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智力,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了。我认为作家只有摆脱智力,才能在我们获得的种种印象中将事物真正抓住,也就是说,真正达到事物本身,取得艺术的惟一内容。智力以过去的名义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也未必就是那种东西。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一经逝去,立即寄寓并隐匿在某种物质对象之中,就像有些民间传说所说死者的灵魂那种情形一样。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我们是通过那个对象来认识生命的那个时刻的,我们把它从中召唤出来,它才能从那里得到解放。它所隐藏于其中的对象——或称之为感觉,因为对象是通过感觉和我们发生关系的——我们很可能不再与之相遇。因此,我们一生中有许多时间可能就此永远不复再现。因为,这样的对象是如此微不足道,在世界上又不知它在何处,它出现在我们行进的路上,机会又是那样难得一见!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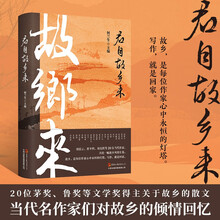

作为曾经名噪一时的权威批评家,圣伯夫所贬低和否定的法国诗人、作家中有不少人,诸如波德莱尔、福楼拜、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奈瓦尔等等,都被时间证明为代表法国19世纪文学成就的经典作家。历史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玩笑?尽管我们可以像普鲁斯特那样追究圣伯夫社会考证学式批评方法上的致命弱点,但埋没如此多的一流作家和诗人的确令人震惊和困惑不解!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我在这里并不想描述或追究存在于法国文坛之外的“圣伯夫现象”,尤其处在近距离观测状态中,明眼人似乎更是一望便知,不用我再来唠叨。事实上,普鲁斯特对“圣伯夫现象”中的非文学性因素并不感兴趣。从法国文学史角度看,对于一种文学批评范式的代表,并对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产生重要影响的圣伯夫式批评理论,为什么历史选择普鲁斯特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经历过写作失败且患有哮喘症,敏感而脆弱的年轻人来加以批判和清算?相比之下,被丹纳称誉为“杰出发明家”,并留下几十卷理论文字的圣伯夫的确是异常强大的,它像尘埃和雾混合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也许,历史只能选择或借助像普鲁斯特和卡夫卡那种正在哮喘的“肺”来呼吸:它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新的气体。而痴肥者则目光呆滞、打着饱嗝并捂住失灵的鼻子。
一般而言,人们只知开创一代风气的作为小说家的普鲁斯特,而对作为批评家的普鲁斯特却知之甚少。事实上,普鲁斯特的文学批评与他的小说同等重要。这不仅因为有关《驳圣伯夫》一书的大量笔记写于《追忆似水年华》之前,并且在其中透露出这部小说的构思和轮廓,更因为《驳圣伯夫》表述了年轻的普鲁斯特对文学写作的本质构成、源泉、特征、方式的独到思考。这种思考在批判圣伯夫的批评模式中为法国新批评派开了先河,而对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奈瓦尔的重新评价使普鲁斯特据此融合他们在真实、幻想、非理性等方面的优势,并提出一系列关于感觉、印象、情感、回忆、欲望,以及时空互置切换的处理方式的见解和技巧,从而开始了他对逝去时间的追寻、再造和沉思,这如同有关玛德莱娜点心的记忆复活于一杯茶的浸泡之中。离开了这种批判性的、包容性的思考,离开了对本国和异国(如罗斯金等)文学传统的切入与再植,同时找到当下的历史机缘与多种写作脉动相互交结、融合的基点,普鲁斯特将难以在某一个向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文学高度。在没有找到自己写作的基点之前,普鲁斯特出版的《欢乐与时日》和未写完便放弃的小说《让·桑特伊》,尽管其中题材与《追忆似水年华》相似相近,但只能使他成为平庸的或者一般性的作家。由此可见,《驳圣伯夫》对于普鲁斯特写作的重要的转折性意义,也就是作为批评家的胆略和识见对于作为小说家的普鲁斯特写作的开启性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说,写作的自觉必然带来文体的自觉:文学边界的位移与拓展以及文学样式之边线的模糊。明确、单一的文学样式对他都不适用了,因为既往作家都无法为他提供解决办法。对他而言,文学样式“就是感受或真实可能体现的形式”。
普鲁斯特的写作因之获得开放的生长的边缘性。这也就是造成《追忆似水年华》既是一部卓越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的内在原因。同样,《驳圣伯夫》也出现文化归属上的困难:法洛瓦认为它已超越于一切文学类别,既不是论文也不是小说,而是一部艺术作品,其中包含着“关于一部书的梦”和“关于一本书的观念”。而我觉得它是散文、小说和论文的混合形式。作者真正沉湎于文学写作本身,因而并不在乎别的什么:那几十本笔记本直到他死后才被整理出版,这与他没有看到他一生唯一的多卷小说完全出齐一样。历史借助那哮喘的“肺”呼吸,但不幸的是,这日渐衰弱的“肺”并不能支撑多久。这使我想到鲁迅那同样哮喘的“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与历史的不可替代之意义。当然,鲁迅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
值得注意的是,普鲁斯特的写作恰恰是在他力量衰竭走下坡路的时刻真正起步的。他封闭于不能见客的房间,进行呼吸道烟熏法,服用麻醉剂;母亲的死使他的精神遭受重创;小说《让·桑特伊》的写作又走进了死胡同,等等。《驳圣伯夫》的写作正是他的文学生命重新起搏的动力之源。这与圣伯夫的情形相反:圣伯夫一贯自我感觉良好、高高在上,把持着进入“经典”之门,连波德莱尔也不得不向他“进贡”香料和蜜糕。看来,“圣伯夫不是因为文章写得不好才是一个坏作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坏作家,对文学的意义和作家应担负的任务完全弄错,所以他才写得不好”。后人的这一判断,我想还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