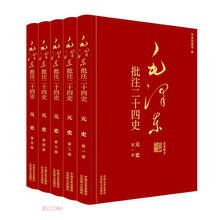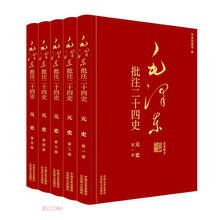客人嘲笑扬雄说:“我听说上古时代的士子,对于人纲人纪,不产生拟订则罢了,若产生拟订,则必定上使君主尊贵,下使父母荣耀。分开人君的珪版,承受人君的封爵,怀揣人君的令符,分享人君的俸禄,身佩青色或紫色绶带,漆红自己的车轮。现在您有幸遇上盛明时世,处于说话无所忌讳的朝代,跟群贤同行列,经历金马门、登上玉堂指日可待了。曾不能筹划一种奇谋,献出一种良策,上向人君解说,下和公卿交谈,目光炯炯如耀眼的星星,口若悬河又如闪闪的电光,合纵连横,议论的人没有谁能抵挡。却反而默默地写作五千字的《太玄经》,似枝叶繁茂四布,独特的解说有数十万言,精深的论说深入黄泉,高妙的论说超出苍天,宏博的论说包括了宇宙,细密的论说渗入了没有间隙的地方。可是做官没有超过侍郎,提拔也才一个给事黄门。想起来黑的莫非还是白的吧!为什么做官不得意呢?”扬雄笑一笑回答他说:“您只想使我的车轮红漆起来,却不晓得一失足就会使我的三族被诛灭啊!从前周朝统治瓦解,宗室诸侯离去,分割为十二国,后合并为七雄,四分五裂,兼并为战国局面。士子没有固定的人君,国家没有固定的人臣,得到士子的君主就会富有,失去士子的君主就会贫困,昂举振奋羽翼,可任意安身止息。所以士子有的自己用袋子装着(求官),有的凿开墙壁逃跑(避官)。因此邹衍凭借奇怪的言辞却取得时世的依赖,孟轲虽然遭遇坎坷,还是受到诸侯们的尊敬。
“现今大汉朝地界东到东海,西到渠搜,南到番禺,北到椒途。在东南设都尉,在西北设候所。用绳索捆绑(罪犯),用腰斩之刑制裁(叛逆)。
用礼乐宣扬(大义),用《诗经》、《尚书》感化(人们)。(遵礼教)构建倚庐,空费三年时光守丧。天下的士子,闻风而动如云而合,好像鱼鳞一样众多杂沓,都从四面八方来营求官位。家家自以为是姬姓、子姓,人人自以为是皋陶的后代。包上头发戴好帽子,丝带垂在腮下而滔滔不绝谈的人,都跟伊尹比拟;可只几岁的小孩子,却羞于跟(图谋霸业的)晏婴和管仲相比较。当权的青云直上,失势的委弃沟渠野外。早上大权在握,则是公卿宰相,晚上失势,就一下成为匹夫。譬如像长江、洞庭湖边的崖岸,渤海中的岛屿,四只大雁停留不显得多,两只野鸭飞走不显得少。从前微子、箕子、比干,去的去死的死,殷商就成为废墟了;伯夷、姜太公归附,周朝就兴盛发达。伍子胥被逼自杀,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存在于世,越国称霸。五毁大夫回到秦国,秦王大喜;乐毅离开燕国,燕王恐惧。范雎凭借打断了肋骨牙齿的身子,却使穰侯魏冉受到危害;蔡泽因下巴下垂闭不住口的形态,而使唐举见笑。所以当国家有大事时,没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樊哙、霍光,就不能安定;当天下太平时,鼓吹章句之学的儒门相与坐高堂、守显职,也没有什么危害的。所以世上大乱,则圣人哲土奔驰天下还不足;世上大治,则平庸之人高枕无忧还有馀。
“上古时代的士子,有的被释放就拜相,有的由平民而成太傅;有的倚着夷门发出笑语,有的横渡江湖悠然打鱼;有的游说七十国君却不遇明主,有的刚(与国君)谈过话就被封侯;有的委屈人君来到陋巷枉顾,有的使人君执帚扫地在前面开路恭迎。因此士子很能够畅所欲言奋笔写作,见有可乘之机即前往而不会受到挫折。现今的县官不请士子,郡官不迎老师,朝廷九卿不对客作揖,将相不低眉自谦。言论奇特的被怀疑,行为特殊的便得罪。因此想谈论的,卷起舌头不言,人云亦云;想投步的,抬脚比量比量才放下脚步,亦步亦趋。假使上古时代的士子处在当今时世,射策对策不是甲科,品行不是孝廉,选拔不是贤良方正,只可向皇帝上疏谏言时道是非,如果说得好最高的待遇不过是待诏;如果说得不好,有所触犯,被皇上知道了便不能任用,又怎么能够得到青色紫色绶带而位列公卿呢?“且我又听说,旺盛的火光会熄灭,隆隆的雷声会断绝。观察雷声观看火光,充充实实。上天收雷声,下地藏火热。显贵人家,鬼也会窥伺他的家室(最终也会家败人亡)。攫取争夺名利的人会身亡,默默无争的人却能生存下去,做大官的人宗族都会危险,守身不出的人性命却能保全。所以说懂得黑和默(不求闻达),是遵守大道的最高标准;清静无为,是游动的精神所寄托的处所;寂寞无声,是白守道德的境界。时代不同事物变化,做人的道理没有不同,上世之士和我换一个时代,也不可知会怎么样。
现在您竟拿猫头鹰耻笑凤凰,持壁虎而嘲讽寿龟苍龙,不也是种弊病了吗!您嘲笑我黑还是白,我也嘲笑您病得很厉害了,碰不到良医俞跗和扁鹊,悲哀啊!”客人说:“如此说,那么没有《太玄》就不能成就名声了吗?范雎、蔡泽以下的人物,何必从《太玄》之义呢?”扬雄说:“范雎,是魏国的亡命之徒,自己打断了肋骨、腰骨,才免于坐牢,缩着身子被人踩着背,才匍匐装入袋子,(人秦)使君主激怒,他离间泾阳君与昭王的兄弟感情,从旁攻击魏冉,取而代之为秦相,是机会适当啊。蔡泽,崤山之东一个普通男子,弯下巴塌鼻梁,满脸鼻涕口水,西人秦见强秦之相范雎揖而不拜,掐住他的咽喉(抓空子)跟他的气势匹敌,又安抚他的背脊最终夺取他的相位,是时势有利啊。天下已经安定,战火已经平息,(高祖)定都在洛阳,娄敬卸下车辆,摆弄三寸之舌,提出不可动摇的国策,把京都搬迁到长安,是机会适宜啊。五帝垂下典籍,三王传授礼仪,百代不可改变,叔孙通起议于乐奏酒醉之时,(使武将们)脱下戎装(排除骄气),于是定下君臣之间的仪礼,是时机适合啊。周代末年刑法侈靡败坏,秦朝刑法残酷严厉,汉朝权宜法式,萧何制定律令九章,是时机合宜啊。所以说,在尧舜时代有人制定萧何律,那么就会错误了;在夏商时代有人习作叔孙通仪礼,那么就会迷惑不解了;在周公辅佐成王时代有人进献娄敬的策谋,那么也就会错误了;在汉宣帝显宦和外戚时代有人谈论范雎、蔡泽的说法,那么就会狂妄了。萧何的规定曹参遵循,张良出谋划策,陈平六出奇计,功勋似泰山高耸,声誉像岩崩远闻,虽然这些人才智充裕,也是碰上时世才可以有作为啊。所以在可为的时世做可为的事情,就顺利;在不可为的时世做不可为的事情,就危险。
“至于蔺相如在秦国章台取得功绩,四老在南山采得荣名,公孙弘从金马门待诏创立了功业,骠骑将军霍去病从祁连山胜仗起家,司马相如从卓王孙那里窃取了财物,东方朔为妻子割得烤肉,我确实不能跟这几个人并列,所以只能默默地独自保守着我的《太玄》经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