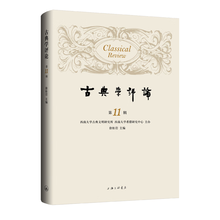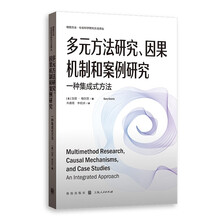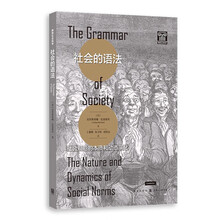调查态度:对新范式的需求
我们写这本书,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看到对于许多调查者来说,外出做调查已经没什么新奇感了,我们想帮助恢复这种感觉。许多调查者似乎把他们的工作当成是一种例行练习,遵守非常明确的规则,拒绝大量的人类灵活思维能力;而我们相信,这种能力的拓展是科学前进、是最令人满意的调查的基础。尽管我们要遵循一种与盛行范式背道而驰的调查范式,但实际上我们相信,“好调查就是好调查”,无论有意义的调查遵循什么样的模式,它都会利用人类心灵那奇妙的灵活能力。下面这个一百年前的故事可以很好地反映我们的调查态度,它有关一次调查培训,其领域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不同。
盯着你的鱼看
S.H.史卡德
1874年4月4日,周六
约十五年前,我进入阿格西教授的实验室,告诉他我已经在理学院登记,了,学习博物学。他提了一些问题:我前来的目的,我的大致经历,我计划日后如何使用我可能获得的知识,最后问我是否希望学习任何特殊的分科。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尽管我希望在动物学的所有学科中都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我打算把精力投入到昆虫研究中。
“你想什么时候开始?”他问到。
“现在”,我回答说。
这似乎让他感到满意,有力地说了声“很好”,他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用黄色酒精浸着标本的大瓶子。“拿着这条鱼,”他说,“盯着它;我们把它叫做haemulon;过一下我会问你看到了什么。”
说完这些他就离开了,但不久又回来了,明确地指导我要保护好交托给我的东西。
“不知道如何照顾标本的人不适合当博物学家。”
我需要把那条鱼放在我面前的锡盘里,偶尔用瓶里的酒精滋润鱼的表层,始终要记着塞紧瓶盖。那个时候还没有磨砂玻璃的瓶盖和形状雅致的展示瓶;以前的所有学生应该会记得那些巨大的圆柱形瓶子和它们的那些易漏、打过蜡的瓶塞,被虫子咬得剩半截,还布满了尘垢。比起鱼类学来说,昆虫学是比较洁净的科学,但教授毫不犹豫地探手到瓶底拿鱼的这一典型做法,却很有感染力;尽管酒精有股“陈腐且带鱼腥的味道”,在这种神圣的地方,我实际上不敢流露出任何的不快,把酒精当净水看待。不过,我还是意识到那种稍纵即逝的失落感,毕竟,对于热心的昆虫学家来说,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鱼并不是件值得称许的事。我家中的朋友如果发现无论用多少古龙香水,都无法驱散我身上那股如影随形的气味,他们也会感到厌烦。
十分钟后,我已经在那条鱼上看到所有我能看到的,就开始去找教授,不过他已经离开了博物馆;我浏览了一下保存在楼上的一些古怪动物,当我返回时,我的标本已经干了。我急忙往鱼身上泼酒精,就像是对突然晕倒的动物进行急救一样,焦急地期待它回复正常的、湿漉漉的模样。这场小风波过后,我只得又紧紧盯着我那不言不语的伙伴。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鱼看上去变得讨厌了。我把它翻来翻去,看着它的脸——恐怖;从后面、下面、上面、侧面、斜面看它——一样恐怖。我绝望了。尽管时间还早,我觉得该进午餐了,因此,我小心地把鱼放回瓶子,带着全然释放的心情逍遥了一个小时。
回来后,我了解到阿格西教授已经来过博物馆,但又走了,而且数小时内不会回来。我的同学们太忙,不能与之继续交谈以免妨碍他们。我慢慢取出那条令人憎恶的鱼,带着无助的感受再次盯着它看。我不能使用放大镜,不能使用任何类型的仪器。我的双手,我的双眼和这条鱼,没有比这更狭隘的活动范围了。我把手指探入它的喉咙,感受它的牙齿有多锋利。我开始数每排有多少片鱼鳞,直到我确信这样做太无聊。最后,一个愉快的念头闪现——我可以描绘那条鱼。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我开始发现这条鱼身上一些新的特征。此时教授回来了。
“不错,”他说,“铅笔是最好的眼睛之一。同样,我很高兴看到你把标本保持湿润,瓶盖也塞好了。”
在说完这些鼓励的话后,他加上了一句:
“恩,它像什么?”
他聚精会神地聆听我简要地叙述那些我还叫不出名称的部分的结构:拱形的腮,能移动的腮盖;头上的孔,厚厚的唇和没有眼睑的眼睛;侧线,刺状的鳍和叉状的尾巴;扁平、弓形的鱼身。当我说完,他等了一下,似乎期待更多,然后带着一丝失望说到:
“你看得不够仔细,”他继续更殷切地说:“你甚至没有看到这种动物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跟这条鱼本身一样,它清清楚楚地就在你面前;再看看,再看看!”他又走了,把我留在懊恼之中。
我感到伤自尊,我感到郁闷。还要再看这条丑陋的鱼!但现在我决心给自己布置任务,而且新发现一个接一个,直到我体会到教授对我的批评是多么公正。下午过得很快。要结束时,教授问道:
“你现在看到了吗?”
“没,”我回答说,“我确定我没看到,但我看出我先看到的是多么的少。”
“还不够好,”他诚恳地说,“不过我现在不会再听你说,把鱼放好回家,也许明天早上你会回答得更好。在你看鱼前我会考察一下你。”这就让人感到不安了。我不仅必须整夜想着那条鱼,在没有对象放在我面前的情况下,我得研究我不知道的,但又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同时,在没有检查我的发现的情况下,我必须在第二天精确地描述一下它们。我的记忆力很差,因此我带着这两个困惑,心烦意乱地沿着查理士河步行回家。
第二天早上,教授那热诚的问候让我感到安心,这里有个人,似乎跟我一样急切地认为我应该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
我问道:“您是否指的是那条鱼的两侧是对称的,器官也是配对的?”他那满怀喜悦的“当然!当然!”令我觉得头晚数小时的失眠是值得的。在他极其愉快且兴致勃勃地——他经常这样——谈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后,我试探性地问他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哦,盯着鱼看!”他说,接着再次离开了,让我自行其是。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听取我的新记录。
“很好,很好!”他重复说道,“但那还不是全部,继续。”连续三天他都把鱼摆在我面前,不准我看其他东西,也不准我使用任何人工设备。“看,看,看”是他重复的指令。
这是我上过的最好的昆虫学课,它的影响延伸到后来的每一项研究的细节中;它是教授留给我、也留给许多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其价值无法估量,买也买不到,我们也离不开它。
我们劝那些想开展有意义调查的人采取类似于阿格西教授要求的那种态度(尽管我们会发现,自然主义调查者要与人类的语言和意义打交道,他们的任务远比考察一条湿透的鱼要复杂得多)。对博士生来说,学位论文很可能是他们要做的第一项重要的独立研究,这种态度尤其重要。对于其中的一部分学生来说,学位论文是研究生涯的第一步,他们在学位论文研究中培养的习惯和态度很可能就是他们以后做研究的习惯和态度。本书中用作范例的很多研究都是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可能对那些处于此阶段的人来说尤其有用。
阿格西教授的教学态度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同样也有启发性。他并没有为学生制定一套可以遵从的规则和程序,他只是告诫:“盯着你的鱼看!”然而,并不是学生的所有观察都有同样的价值。观察的有效性源自于摆在学生面前的那条湿透的、无生命形式的鱼和从那些观察出发的逻辑引申。这非常类似于我们要在本书中提出的过程。观察、记录、分析、反思、对话和再思考这样一些过程,都是我们力图提出的调查过程的核心部分。所有部分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被观察事件所在的语境。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进一步考察语境的重要性。
社会环境中的调查
在本书的这一开篇章节中,我们简略地提到善于人类互动研究的调查者在工作中经验到的某些挫折。这些挫折似乎不完全源自其调查领域的复杂性,更是源于一种盛行的调查模式,该模式不允许使用某些潜能巨大的调查工具和程序。本章探索某些已被试验过的候选程序,并且简要地描述一下当前对调查范式转换的看法。结尾简单地考察了社会语境在做自然主义研究中的关键作用。
在《运动心理学家》(The Spart Psychologist)的一篇文章中,马腾斯(Mar-tens,1987)讲述了他自己作为调查者的经历:
我用研究所学到的科学方法研究运动心理学大概有十五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这些方法越来越感到不满,不是因为我对研究现象缺少兴趣,因为现在我越发着迷于运动心理学的题材。事实上,我变得不满于用来研究我们领域中的现象的那些方法,但我并不完全知道是为什么。我不能理性地说明原因,但是就情绪而言,对于忠实地理解人类行为来说,这些方法并非“似乎是正确的”(P.29)。
稍做调整,马腾斯的叙述就很可能描绘了许多调查者的经历,他们主要的关注点就是人类行为和该行为发生的环境。教育组织的学生经常失望于“最好的”调查方法在获得重要问题的答案上的无助。如果马腾斯的感觉是正确的,如果它反映了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的普遍困境,那么它暗示的是,被看作是“最好的方法”不够好。
在《社会公益服务评论》(Social Service Review)的一篇文章(Heineman,1981)中,海涅曼提到社会工作领域中方法论和设计的影响:
社会工作调查的盛行模式设置了调查设计层次,它涵盖了整个的范围,从最不 科学的到最科学的,而且依它们满足预测标准及随带要求——比如实验操作、控制组和随机化——而得到排列(P.374)。
她继续说到:
问题不是这些关于构成好科学和好社会工作调查的假定从不导向有用的知识,而在于它们是被规范性地使用,而非描述性地使用,来规定某些研究方法论和禁止其他的方法论(P.374)。
海涅曼声称,当前科学的社会工作概念化的规定性本质(这体现在首选的研究设计和方法论形式中)有力地决定了实践的本质,而不允许实践决定科学研究的形式。
对于本书的作者来说,马腾斯的体验和海涅曼的评论听起来是对的,而且我们猜测它们对于许多读者来说也是对的。我们在对底层假定,尤其是知识的客观性假定不做任何置疑的情况下,轻易接受科学方法的规定。自小学起,我们就听到了对科学方法优点的颂扬,完全吸收了传达给我们的、反映它对人类繁荣所做贡献的历史。由于科学方法被过分简化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所以当我们取得的结果无法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时,这种成见经常导致我们质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能力。我们固执地期待统计程序和计算机能力,以为能用它们来量化和处理在社会环境中碰到的微妙、复杂的差异,从不怀疑客观的量化可能正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
马腾斯发现他自己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我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心理学——我称之为学院运动心理学和实践运动心理学。它们导致我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学院的、科学的和抽象的,另一种是实践的、应用的,以及在某些人看来,神秘的。为什么这两种运动心理学会分道扬镳?我认为,答案在于运动心理学家对何为合法知识的理解(P.30)。
在马腾斯看来,学院运动心理学主要关注的是科学规则的应用,其应用方。式据说是行为研究者可接受的。然而,他发现第二种生活,即作为实践运动心理学家的生活,更有效果,因为,相比起他用正统科学方法来研究运动心理学而言,他用实践心理学获得的知识更多。马腾斯认为,鉴别和获得“合法知识”的两种方法间的这种分裂,反映了库恩(Kuhn,1970)那里与范式危机有关的东西。
在库恩看来,范式提供了看世界的方式。它通过提供假定、规则、指导和“常规科学”的实施标准,对研究领域施加影响。在某一研究领域,科学家所做的已被接受的工作就是挖掘范式蕴含的细节,与此同时,履行范式的承诺。但是,就如库恩在许多不同领域中表明的,这种工作不可避免会制造反常,而盛行的范式不可能全部容纳。这就为能更好地说明反常的新范式铺平了道路(如太阳中心说取代地球中心说的宇宙观),并且使新阶段的常规科学得以启动。然而,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一般不那么顺利。某个领域内旧一代的、已确定地位的科学家,是围绕更早的范式来开展其工作的,他们控制了科学工作奖励的那些规则。冲突会一直持续,直到新兴的范式变得盛行,而通常不是到旧范式的消亡,还会有最后一批保护旧范式的杰出科学家。
在《社会公益服务评论》中,霍沃思(Haworth,1984)的一篇文章考察了库恩的论点对社会科学的寓意:
无论人们是否赞同库恩的历史分析的所有寓意,有个后果是引人注目的。自1962年后,不断增长的“范式意识”一直在削弱社会科学家的假定。在压力的驱使下,直觉的、暗含的东西变得更明显……这一过程在前范式阶段的社会科学中更为混乱,在这种科学中,假定通常是不加质疑地借用、武断地学习、顽固地坚持的(P.351)。
关于范式转换,最全面的陈述可能是由施瓦兹和奥格威在他们的专著《自发范式:改变思维和信念模型》(Schwarz&Ogilvy,The Emergent Paradigm:Changing Patterns of Thought and Belief,1979)中提出的。他们对广泛的研究领域中正出现的情况做了分析,它们包括物理学、语言学和艺术;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新的整体范式正在出现,它对目前主导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假定和信念构成了挑战。对新范式的追求,最全面地体现在知识换代和古巴、林肯(Guba,1978;Guba,1981;Guba&Lincoln,1981;Guba&Lineon,1989;Lincoln,1989;Lincoln&Guba,1985)在教育领域所做的研究中。这一新范式最初被古巴和林肯明确地表述为“自然主义”范式(Guba,1981;Guba&Lincoln,1981;Lincoln&Guba,1985),尽管近年来,由于“自然主义的”这个词语的一些寓意,他们更愿意称之为“建构主义的”而非“自然主义的”(Guba&Lincon,1989)。不过,本书在指称新范式和与之相联的研究模式时,我们将继续采用“自然主义的”这个术语。
古巴和林肯的著作和工作对目前这本书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细致地考察了盛行范式的假定和困难,系统地阐述和扩展了新范式的哲学基础和程序建议,为在新范式下的研究配备了初步的保护法典,担起了范式危机时期的主要战役和争论。尽管我们不如林肯和古巴那样明确新范式的精确本质,但我们确实赞同林肯(Lincoln,1989)的看法:该争论牵涉到“整体范式”的转换,不能靠修补方法或修补孤立的科学研究原理来得到解决。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