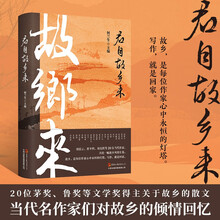纸手铐:一部没有拍摄的影片和它的43个变奏影片《纸手铐》在三个层面上展开。
在第一个层面上,该片将以故事片的虚构形式直接呈现一个人的真实经历。那人作为一名“思想犯人”,70年代曾在一座极为偏僻的、近乎抽象的监狱里被囚禁了数年。
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种匮乏在这座监狱里也有所反映:该监狱关押了近千名囚犯,但只有十来副铁铐。这对于维持正常的监狱秩序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纸手铐被发明出来。囚犯如果违反了狱规,其惩罚不是直接用铁铐实施,而是以监狱管理人员即兴制作的纸手铐来象征性地铐住囚犯的双手,惩罚时间从三天到半个月不等。惩罚期间,若纸手铐被损坏,则立即代之以铁铐的真实惩罚(铁铐每副重达30公斤)。如果惩罚期满时,纸手铐仍然完好无损,则不再实施铁铐的惩罚。
纸手铐被发明出来之后(无论它是作为一个玩笑,还是作为欠缺物质性的无奈之举),囚犯们为逃避铁铐的惩罚,全都神经质地、心力交瘁地保护纸手铐不被弄坏。长年累月这样做,导致囚犯在心灵的意义上普遍患了“纸手铐恐惧综合征”。
该片的主角(叫什么名字不重要,我们暂且称他为“那人”)对纸手铐的恐惧,起初体现为对记忆的恐惧,而记忆是他维系与入狱前的自由生活之真实关系的唯一途径。
他的父亲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民间剪纸艺人,其“纸鸟”作品系列千姿百态,广为人知。
影片主角自小耳濡目染,心追神往,受父亲影响之深可想而知。通过“纸”来表达飞翔的愿望,成了他内心深处萦绕不散的一个深度情结。
档案是这样记载那人的入狱原因的:胆敢将主席头像裁去一半,折成纸鸟,到处飞着玩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人暗恋上了一个女孩。他发现女孩每天黄昏都会独自一人在空地上看飞鸟,有时会痴痴地看上一小时。于是那人突发奇想,决定用纸折一只鸟送给女孩。但他找不到中意的纸。物质匮乏的年代,好纸得用来印制主席像。那人只好用主席像反过来折(纸张太大,就裁去一半)。女孩得到了纸鸟,欣悦之余,将纸鸟带回家中,拆开来想照原样折出更多的纸鸟。女孩家长发现纸鸟是用主席像折叠的,而且是半张主席像。这可是个大案。那人就这样被抓进了监狱。
在监狱中,那人必须与自己的童年记忆、青春期记忆决裂:同样是“纸”构成的现实,从前是关于飞翔的,现在则是关于禁止和惩罚的。最终他对纸手铐的恐惧变成了日常生活。他终日沉湎于纸手铐幻觉之中,双手在任何时候都呈现出被铐住的样子,甚至在梦中也是如此。并且,他不能忍受纸撕碎时发出的声音,他对那个声音极度敏感,深怀恐惧。
纸手铐的“囚禁”主题变形为“听”:对纸撕裂时发出的微弱声音的一种听,非常遥远的、几乎没人在听的一种听——在纸里听到铁,在各种声音中听到纸。
一种连它自己都不是的声音,可以任意被改写为任何一种令人恐怖的声音。影片的主角第一次听到那声音(纸手铐被撕碎的声音)是在梦中,当时他正好梦到一枚伸手可摘的苹果,他双手向上去摘那苹果时,铐在手上的纸手铐撕碎了,他听到了一种类似于刀片在割、锉子在锉的带铁锈的声音——与其说是听到的,不如说是感觉到的。
诸如此类的细节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思想的隐喻,但对那人来说则是每天的现实。以致出狱多年之后,这种“纸手铐恐惧综合征”仍然在他身上起作用。他双手被无形的、内心的手铐固定在某处,永远呈现出被铐住的样子。他只有在“被铐”的状态下才有安全感,才能感到“手”的存在,才能安然人眠。他依靠对纸手铐的想象活在世上,纸手铐对他来讲既是恐惧又是一种类似于乡愁的“迷恋”。他只能在幻想中但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听到纸撕碎的声音,比如,拆开一封信的声音。出狱后,他收到过那么多来信,但他从不拆开。那些来信中有那女孩的来信吗?女孩一直在等他吗?在命运的意义上,他将错过什么呢?影片的第二个层面是对上述故事的即兴讨论。
这个部分将用纪录片的手法拍摄。讨论不加预设,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命题:其一,想象中的监狱比真实的监狱更为可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关在里面,但又可以说人人都关在里面。这个监狱是用可能性来界定的。
其二,纸手铐带来的“不自由”的恐惧在于:它太容易挣脱,因为它取消了“铁”这样的物质现实,囚犯一不小心就挣脱了它,完全不想挣脱也不行。纸手铐一撕就碎。
在这里,惩罚变成了游戏和玩笑。一种肉体的悲剧结束了,代之以一种心智的喜剧。
其三,考虑虚构的能量。纸手铐是站在虚构这边的,但它本身构成了一种真实。被纸手铐铐住的是我们身上的“非手”,纸耳朵听到的是众声喧哗的“聋”。
其四,纸手铐所包含的“非手铐”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非手铐”的存在证实了“非手”的存在,在纸手铐里我们看不到真正的手。
其五,纸手铐发明了一种“非肉体”的惩罚。在纸手铐中,作为肉体的手是不存在的。但如果手铐不是铐在手上的,那么它铐在什么上呢?如果最严酷的惩罚不再施加于肉体之上,它又能施加于什么上呢?答案似乎也就深藏在问题之中:既然惩罚的对象不再是肉体,那就必然是心灵。曾经以物质的(铁铐的)形式降临在肉体上的灾难,现在以非物质的(纸铐的)形式深人心灵、想象、直觉、梦境之中。囚禁内化了。
囚犯本人是怎样成为他自己的狱卒的?在影片的第三个层面,参与讨论的人一个个销声匿迹,只剩下孤零零的、手写体的文本。一种清洗液开始清洗影像,它同时被涂抹到影片的声带上。起先,人的声音没有了:交谈声变成了哑语,咳嗽声哽在喉咙里。接着,物的声音也没了:电话被挂断,打字或书写的声音被橡皮擦擦去,仅有的一支枪是哑火的,不能发射子弹。最后,电影放映的声音也消失了,放映机不再转动,但影片继续在放映。清洗之后,只剩下纸被撕碎的声音:各种不同的撕法,各种不同的纸。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