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的天堂
有
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生时间,一直众说纷纭。一说一九二七年,另说一九二八年。多年以后,他在护照上填写的出生时间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老二路易斯·恩里克小他一岁,一直以为自己生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看到哥哥的护照后,他不知该如何是好:“见鬼,这么说我是个六月早产儿,要不就是加博的孪生弟弟!”这实在是太糟了,尤其是在后来,哥哥出名了,弟弟可就遭殃了,无论如何,履历都大有问题,因为紧跟着他的还有个妹妹呢。妹妹玛尔戈特的出生时间被告知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假如路易斯·恩里克的生日往后推迟四个月,那么不仅她的诞辰要成问题,而且他们可怜的母亲也受不了哇:她必得每十个月生一个孩子,并且连生三个。
更有甚者,当时他们住在阿拉卡塔卡,外祖父性情中人,参加过“千日战争”,退休后既接纳私生子,又领养孤寡女,把家庭弄得像个小剧场。外祖母虽然敦厚贤惠,却有一肚子奇奇怪怪的故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便是伴随着外公的历史、外婆的想象度过的。多年以后,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不经意中有了一次“归根之旅”:“母亲叫我陪她去卖房子……”
母亲叫我陪她去卖房子。当时我家住在一个遥远的小镇。那天早上,她来到巴兰基利亚,却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她东询西问,知情人让她到世界书店及周围的咖啡馆找一找。那些都是我每天早晚两次必去之地。我在那儿会我的作家朋友。那个为母亲指路的人提醒她说:“小声点,他们可是些书虫儿”。12点钟,她蹑手蹑脚地绕过书桌,来到我的身边。她看着我,笑容黠慧。那是她美丽时光的见证。没等我作出反应,她开腔说:
“我是你妈。”
她变化不小,所以乍一看我没能认出她来。她45岁,生过11个孩子。也就是说,她怀孕整10年,加上相应的哺乳期,多少有点未老先衰了。她满头堆霜,眼睛也好像大了一圈。那会儿她正透过一副老花眼镜愣愣地盯着我瞧。她穿着丧服,正严格地为她的母亲服阕。当然,她依然保持着婚纱照上的古典式华美,且又因成熟而更加风姿绰约。在拥抱我之前,她先以惯有的郑重对我说:“我是来请你陪我去卖房子的。”
无须任何说明,我就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房子。因为,对我们而言,这世上只有一处房屋属于我们:我外祖父母留在阿拉卡塔卡的老屋。那也是我有幸出生的地方,但8岁离开之后一直没能回去。我刚刚辍学,放弃了攻读3年的法律,时下正致力于阅读一切到手的书籍,或者没完没了地吟诵不可再造的西班牙黄金世纪诗歌。而那些借阅的翻译作品使我获得了创作小说的技巧。我已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6篇小说,因此而得到了友人的鼓励和一些批评家的关注。再有一个月就是我的23岁生日,逃过了兵役并有了两次淋病经验。我每天抽60支劣质香烟,简直肆无忌惮。我辗转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边的卡塔赫纳和巴兰基利亚,靠《先驱报》的那点儿几乎了不可见的专栏稿酬活得像个一无所有的国王,夜幕降临之际则恨不得以尽可能奢侈的方式拿天作被拿地当床。然而,生活的混沌和希望的渺茫仿佛不仅于此,一群形影不离的哥儿们居然突发奇想,要搞一份可怜兮兮的刊物。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
此外,我比时尚整整超前了20年:穿花衬衫,着牛仔裤,长发蓬乱,须如蔓菁,脚下还朝圣般地踢踏着一双凉鞋。此般模样却非出于嗜好,而是因为太穷。一次,在电影院的黑暗之中,一位异性朋友对另一个人说:“可怜的小加博算是没得救了。”她当然不知道我就在旁边。
因而,当母亲叫我一同去卖房子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当她说没有足够的旅费时,我却碍于面子说我的那一份由我自己负担。
我在报社里根本无法解决这个负担。他们每天只付给我的专栏三个子儿,偶尔因为哪个撰稿人的阙如轮到写一篇社论也只有4块钱。而这些勉强够我苟活。于是我想到了预支,经理却告诉我说,我的欠款已经超过了50比索。终于,我做了一件朋友们无法想见的事情:我出了书店,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门口堵住了书店老板、卡塔卢尼亚老头堂拉蒙·温耶斯老师。我开口跟他借6块钱。可是他搜索遍身只找到了6块。
无论母亲与我,都不曾料想这么一次单纯的两天之旅会对我产生命定般的作用。从此往后,即便我寿命再长、工作再勤奋,也无法穷尽由此萌生的故事。而今,我已经75岁出头,我知道那是我作家生涯、甚或一生中迈出的最最重要的一步……(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生活》,西班牙蒙达多里出版社2002年版,9-11页)
在此之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记忆尚未受到理想主义的浸染。因此,对他而言,故乡阿拉卡塔卡是加勒比海边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一条小河从镇边匆匆流过,河水清澈见底,河床卵石满布。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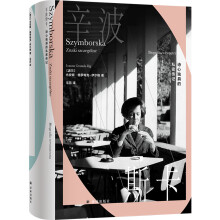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
《百年孤独》在马尔克斯构建的虚拟世界中达到了顶峰。这部小说整合并且超越了他以前的所有虚构,从而缔造了一个极其丰饶的双重世界。它穷尽了世界,同时自我穷尽。
——巴尔加斯·略萨
他是所有语言中最伟大的作家。
——比尔·克林顿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唯一没有争议的一位。
——韩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