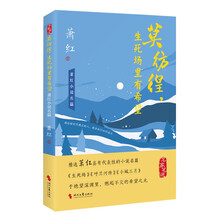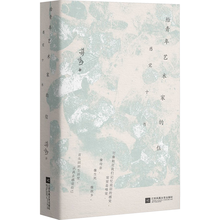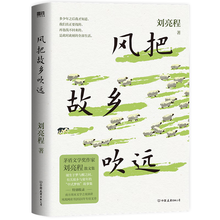对于这个无法对付的儿子,母亲还是母亲,只能是父亲的缘故。原来,在我出生前后,父亲对于那些旅行中的南画家和俳谐师等人物,或留宿家中,或当成朋友,净和这些古里古怪的人来往。而父亲自己也是个具有这种无用的怪癖的人物,所以照母亲的说法,这种怪癖也传给了我。
我如今的确感到我的身体里流动着许多父亲的血液。从风貌上说,我很像当年的父亲——人们都这么说。看了照片就更明白了。近年来,甚至有人错把我当成了父亲。从声音上说,我在楼上说话,连母亲也分辨不出是我的,还是父亲的。不光是外貌,从爱好上说,我喜欢搜集各种无用的东西,这一点也很像父亲。从书画、古玩,到各类动植物。父亲还养过鹤。据他说,除了学习音曲之外,其他什么都干过。他骑过马,迷恋过摄影。刚刚进口自行车时,他也曾极爱一时。父亲在二十岁前拿到医师证明,便及早自立,为此,他年少时的好奇心都一一得到了满足。分家时父亲没有从祖父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能安贫乐道,可以说他是出自真心的爱好。父亲只是从赴东都求学的经费中搜集了一点文入画。当时他很爱读鸥外渔史的著述,后年又敬慕漱石先生,收藏了先生亲自赠给他的书画、扇子等物。
我兴趣广泛,又有点这山望那山高,但我对于读书、园艺和美术的爱好逐年增加。父亲总是把“俗气”一词当作批评一切的标准。我想,洁白或许是他的道德的理想。他是个讲究气度的人,但同时又有点难以理解的懦弱性。两三年前,去东京的时候,我听母亲说,他们一同去和服店,无法任意挑选,因为父亲指责母亲说:“人家店里摆得整整齐齐,你一挑不就乱了吗?”
“有个词儿叫‘略带微醺’,而我却是‘略带微愁’,反而感到高兴。这种高兴总有点怪哩……可我喜欢。”我记得父亲有一次这样说。伊利安·库帕说过:“诗的痛快中有欢乐,这只有诗人知道。”若果如此,我的父亲就是诗人。父亲先称镜水后称枭睡,如今号枭叟,是私淑子规的俳句诗人。他对文学很敏感,我住在贫穷的幽灵坂这地方时,父亲每次给我写信,总是在信皮上写着“幽丽坂”这个地名。
“镜水”一词的由来是,他的故家在八镜野,旁边有条河。镜水之父号镜村,又自名镜野隐逸,英年早逝,遗《镜村诗集》一卷。我家代代行医,又是农民。虽说不是小泉八云,但我的血液里,不论父方还是母方,都没有一滴商人的血。镜村之父椿山应召做了水野土佐守的典医,最后没有走入仕途,只是个村翁,喜欢和歌。一个一个诗魂是我家的遗产。有人说,天才是突发的东西,遗传只会是能才。要是这样,我什么都可以。只是我和弗里德里赫·尼采都是夸耀祖先的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