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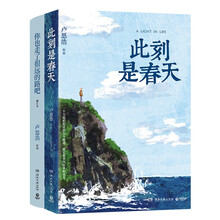








文学在岳雯眼里是个鲜活的存在,不是可以用条文来规定的,不是可以用概念来规范的,她拒绝教条的框定,与成规保持距离,使自己眼中的文学世界拥有了开阔的生成可能性。
岳雯是个素质全面的研究者和评论者,才情、天分、勤奋,使她在所经营领地里已经焕发出了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光彩。文学在她眼里是个鲜活的存在,不是可以用条文来规定的,不是可以用概念来规范的,她拒绝教条的框定,与成规保持距离,使自己眼中的文学世界拥有了开阔的生成可能性。
气象开阔,境界始深
——2007年的长篇小说
在《浮士德》里,浮士德面对浩瀚如大海沸腾如熔岩深邃如星空的生活,怀着幸福的预感,对这一瞬间失声叫道:“你真美啊,请你停留!”这个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回响着每个人隐秘的内心冲动:让飞逝的时光停驻,让流淌的记忆定格。然而,属于2007年的波澜壮阔终将翩然而去,能够把握得住的不过是回望的心。由此,文学承担起补偿的功能:它让我们穿越重重表象与幻觉,追问时代的精神本质;它让我们拂去现实里的经络交错,分辨鲜活致密的人格质地;它让我们在茫茫不可知的惘然里,探求深藏于人心的秘密;它亦让我们在喧嚣的话语迷雾中,得以触摸历史的温热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篇小说以其鸿篇巨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文体。这么说,并不仅仅因为年均一千多部的长篇小说出版量已然成为文学出版的主要格局,也不仅仅因为长篇小说不言自明地成为衡量作家创作成就的参考指标,更重要的是,长篇小说密布着时代的呼吸,向我们展示着几代人在精神探索上的诸种可能性。
2007年,是长篇小说再次占据文学生活主流的一年。写作者们对现实生活的沉着观照和秉笔直书成为这个年份令人最为感奋的文学景观。这一年,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有《启蒙时代》(王安忆)、《人间》(李锐、蒋韵)、《山河入梦》(格非)、《刺猬歌》(张炜)、《风声》(麦加)、《桃花》(张者)、《高兴》(贾平凹)、《白麦》(董立勃)、《吉宽的马车》(孙惠芬)、《我叫刘跃进》(刘震云)、《初夜》(唐颖)、《青木川》(叶光岑)、《等等灵魂》(李佩甫)、《道德颂》(盛可以)、《黑白》(储福金)、《白纸门》(关仁山)、《轻雷》(阿来)、《所以》(池莉)、《致一九七五》(林白)、《戎装女人》(刘静)、《机器》(肖克凡)、《赤脚医生万泉和》(范小青)、《我是你儿子》(孙睿)、《野草根》(徐坤)、《女心理师》(毕淑敏)、《特务连》(徐贵祥)、《天长地久》(张海迪)、《磨尖掐尖》(罗伟章)等。这些小说的面世,标志着作家们在用密集的语词编织着这个时代的精神图景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他们对小说艺术所保有的执著的热情。在集中描述长篇小说的年度状况时,我愿意用“气象开阔,境界始深”来概括其整体的文学气韵;我要向写作者们表示敬意,正是他们艰苦的创造,使这个匆忙发展、迅速变革的时代为精神的传承而驻足沉思。
记录时代的荣光与艰辛
在汪洋恣肆、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里,先在地潜伏着一个坚硬的内核,它几乎决定了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所存在的理由和野心。这“内核”,即是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与认知。致力于表现“历史表象中的历史灵魂”的长篇小说天然地成为时代的投影,它不仅从时代这艘大船的激流勇进中吸取力量,更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有效地参与了新的社会历史构型的完成和文化史、心灵史的建构。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关注社会转型期间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越来越成为当今作家们的一种自发意识和自觉担当。
2007年,继《秦腔》以后,贾平凹携《高兴》归去来,一时间备受关注,《高兴》亦被称之为“具有时代症候和文学史价值”的典型性文本。如果说,《秦腔》是写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瓦解和破碎的过程的话,那么,《高兴》可以看作是这一叙事的继续与发展。刘高兴和像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城群体是如何在城市中挣扎求生,边缘小人物的灵魂又是如何一步步靠近城市,这正是《高兴》所关注的时代主题。
“我想,刘高兴和他那个拾破烂的群体,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是别一样的生活,别一样的人生,或许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吧。”这是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里说的话,也可看作《高兴》的写作的初衷。于是,我们看到一双悲悯的眼睛,犹如一束追光,注视着从清风镇来到西安的刘高兴和他的伙伴五富,注视着他们满心怀着对城市的向往却屡屡碰壁,在遭遇巨大生存困境时只得以拾垃圾为生,注视着他们对尊严的渴求与维护,也注视着那时代魅影背后普通民众相濡以沫的温情。明亮坚实的叙事,却寄托着作家巨大的苍凉感。
“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这是贾平凹们的宏大的意图,内里透露的是巴尔扎克式的野心。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遭遇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是多么幸运,个人在与社会历史情境的狭路相逢中碰撞出耀眼的火光。小说家们在生动复原生活场景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捕捉到了个人内在的丰富性,《高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住了。小说家沉潜到生活内部,引入了新鲜的材料,使我们对刘高兴这样的拾荒者的看法突破了既有的格式。他爱清洁,有尊严感,他还常常在收破烂的间隙吹箫,他用他的智慧试图解决乡人们的生活难题……更重要的是,他“高兴”地活着,努力接受并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刘高兴是在以一种兴高采烈的心性活着,那么,本年度的另一部重要小说《吉宽的马车》则提供了讲述“乡下人进城”的另一套语法。小说叙写了歇马山庄有名的懒汉申吉宽是如何在对城市的拒斥中一点点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城市的过程。这位喜欢《昆虫记》、没日没夜在坑洼不平的乡道上转悠的马车夫,是乡村生活的忠实拥趸者。在所有乡村男人都义无反顾地奔赴外面的世界去打工的生活背景下,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公认的懒汉。然而,许妹娜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存在状态。这个进城打工时被小老板看上的山庄女孩,在回乡办嫁妆时与吉宽相爱,随即又流落城市。吉宽也不得不告别乡村乌托邦,奔赴城市来寻找他自己的命运。在城市与乡村的来回迁徙中,众多人物形象如一棵大树上的叶子般渐次出现,构成了一幅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城市“外来者”的群生相。吉宽的命运是小说叙事的内驱力,在这层命运帷幕遮盖下的,是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在人物内心深处的纠缠、挣扎与碰撞。这就是孙惠芬孜孜以求的一个人以及更多人的“内心风暴”。
“做时代的记录者”不仅意味着对当下中国现存生活境况的发现,更意味着在巨大变革中对某些失去了的价值体系的呼唤与重建。在这个维度上,肖克凡的《机器》散发出天真果敢的工业时代的气息,有着对劳动时代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热情洋溢的讲述与回望。小伙计王金炳和小女工牟棉花怀揣着对“机器”的向往付出了艰辛的代价,只有在解放后才真正成为“工人”。对劳动的热情和对“机器”的热爱使他们双双成为“劳模”。“机器”象征着他们的命运,也映照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女兵出身的刘静在《戎装女人》以安详从容的笔调叙写了女军人吕师大校以及她身后站着的一个军队世家。军人的一切优秀品质,都在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琐碎里一一被打磨,放大,构成动人的向善的力量。刘静的笔触是宽阔的、温暖的。这宽阔是对鸡零狗碎生活中人性宽广的确证,这温暖是对经历复杂世态后人心美好的信仰,因此更具力量。
在此,小说家们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精神姿态,敏锐地提出现实生活所面对的重大问题,时刻保持警醒,努力深入生活现场,打通血脉,获得对广大民众深切而真实的精神观照。他们践行着小说给我们的承诺,即将“这一个”丰富的心灵向现实展开,理解“这一个”的境况,由此获得对广阔时代和广袤生命的深层理解。于是,在时代的大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群坚强独立的普通人踽踽前行的身影。2007年的文学版图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普通人的存在,才动人,才辽阔。
……
序:我们都该发现自己的沉默所在
气象开阔,境界始深
——2007年的长篇小说
在路上,回归与重塑
——2008年长篇小说扫描
“时代”的胜利与“人”的退场
——2009年长篇小说一瞥
长篇小说和它面对的世界
——以2010年长篇小说的主题形态为例
所有的过客都到齐了
——作为证词的2011年长篇小说
图画、感觉与词语
——观察2012年长篇小说的一个角度
穿什么样的衣裳,就有什么样的灵魂
——2013年长篇小说一瞥
恍惚、童心及其他
——谈红柯写作的三个维度
无法简化的葛水平
安妮宝贝:无法抵达的追索
上海传奇的另一种写法
——论虹影小说中的都市空间想象
发现笛安
对峙与复归
——关于葛亮中短篇小说的一些断想
小说家东紫与好人威慧贞
伤口的故事
——苏兰朵论
“兔八七”长大了
——霍艳论
怀乡者说
漂浮在叙述之流上的“个人”
——“七十年代人”观察
沉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