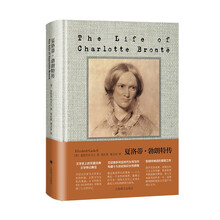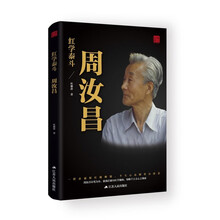五、大革命的风云变幻11926年的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国民政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武汉三镇成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时,父亲已内定_出任浙江省政府的秘书长,只等北伐军光复浙江后即去杭州上任。可是北伐军的进攻受挫,孙传芳又把响应北伐军的原浙江省省长夏超赶出了杭州,父亲_的工作也变得不可测了。于是党中央改变计划,决定派他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原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1926年底,父亲和母亲离开了上海,这次是母亲主动要求同行的,她从家乡来沪后,还未离开过上海,为了这次远行能如愿,她没有把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告诉父亲。
1927年初的武汉与上海的气氛大不一样,国民政府刚刚在外交上打了个大胜仗,收回了汉口的英租界,一洗“五卅”运动时上海英租界的巡捕滥杀我爱国同胞的耻辱,也洗刷了几十年来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丧权辱国的种种奇耻大辱,大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像火山喷发的岩浆般奔泻于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除了穿军装的男女军人,随处能见到摇着小红旗,喊着口号的各个行业的工人自卫队、学生宣传队、妇女工作队等忙碌的身影。父亲和母亲一踏上汉口的码头,就立即融入了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
在武汉的头三个月,父亲的主要工作是在军校讲课,课目有:什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国民革命军的政治目的是什么,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等。那时学校刚创办,缺椅少桌,也没有大课堂,上课时教官就站在操场中央的桌子上讲,学生则围在四周听。因为没有扩音器,教官必须直着嗓子吼,所以一堂课下来十分吃力。但因为只是单纯的讲课,晚上便有空闲的时间去找老朋友聊天。那时聚集到武汉的父亲的熟人真不少,像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李汉俊、恽代英、李达、邓演达、周佛海、陈公博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同事也有不少在这里。但他们多半比父亲忙,有的简直忙得焦头烂额,通常不易见到。
那时武汉正传布着农民运动过火的流言,说农民协会不分青红皂白,把北伐军军官的家都抄了,还让军官的父母和亲属戴上高帽子游街等等。母亲分配在农政部工作,她也听到过这些传闻。父亲还听说党中央内部对这种现象有不同的看法。父亲在见到瞿秋白和陈独秀时询问了此事。陈独秀对此很恼火,认为无产阶级需要发动广大的农民同盟军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工农联盟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决定因素,但是农民运动的发动要慢慢来。目前湖南、湖北农民协会动辄给土豪劣绅戴高帽游街,这是侮辱人格的幼稚行为。尤其是把许多革命军人在农村的家给抄了,还枪毙了他们的家属等等。这种做法,是在给革命帮倒忙,弄得农村人心惶惶,势必将直接影响到北伐军的士气,甚至危害国共合作的基础,使目前大好的革命形势倒退!他主张坚决制止农村中的这种过火行为。
瞿秋白的观点则与陈独秀不同。
他递给父亲一篇毛泽东的文章,说:“你看看润之同志的这篇文章,我是赞成他的观点的。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要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光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发动最广大的贫苦农民自己起来革命。现在南方各省农民协会正在做的就是这个工作。谁都知道,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难免泥沙俱下,有些幼稚过火的行为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评价它,是看主流呢,还是只注意泥沙。我赞赏润之同志的评价:农民运动好得很,不是糟得很。”父亲同意瞿秋白的意见,而且明白了在农民运动过火这个问题上,中央内部的分歧很大。
不过,进入4月份,这个问题的争端暂时被压了下去,因为蒋介石叛变了。14月初,中央决定调父亲去编《汉口民国日报》。这报纸在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报纸,也可以说是共产党掌握的第一张大型报纸。报社社长是董必武,总经理是毛泽民,父亲是总主笔,编辑人员除了一位国民党左派,其余都是共产党员。报纸的编辑方针也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确定。它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中央日报》成为武汉相互对峙的两大舆论阵地。
父亲接编报纸才几天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突然袭击和屠杀共产党人,血腥镇压上海的起义工人。武汉震惊了,《汉口民国日报》开始整版整版地刊登声讨蒋介石的文章。
父亲撰写的讨蒋社论就有《革命者的仁慈》、《袁世凯与蒋介石》、《蒋逆败象毕露了》等五六篇。然而,群众讨蒋的热情虽高,军队讨蒋的行动却拖延不决,原因是武汉国民政府掌握的军队,除了叶挺的独立师,其他都隶属于国民党,这些军队的将领并不热心去讨伐他们的“校长”蒋介石。结果东征讨蒋的计划终于流产而改为继续北伐。其时汪精卫从国外回到武汉,宣布与共产党继续合作,国民党中央也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了他的总司令的职务。当时汪精卫的这种“革命”姿态迷惑了不少共产党人,其中就有陈独秀。
4月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蒋介石叛变后的政治形势,指出原来的工农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已经破裂,今后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是工农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因而要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合小商人、小地主,反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新旧军阀。关于农民问题,大会指出“国民革命应首先是一个农民革命”,提出要加深农村革命进程,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解除土豪劣绅的武装,建立乡村自治政府,组织农民自卫军;同时又提出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五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是正确的,但并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汪精卫采取了两面派手法,以保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借口,阻碍了决议的实行。陈独秀则为了保持与国民党左派的政治联盟,对汪精卫限制农民运动的措施及暂缓东进,先行北伐等重大决策,都采取支持或默认的态度。当然,这里也有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在内。
大约在5月间,有一天陈独秀约见父亲时对他说:“《汉口民国日报》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现在外面都在造共产党的谣,说什么‘共产共妻’,所以你在报上还是少登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父亲说:“《汉口民国日报》没有记者,所有的消息都是工会、农协和省政府供给的,这些消息我都看过,说的都是实际情形,无非是揭露土豪劣绅,没有‘共产共妻’的消息呀!”陈独秀说:“那是他们造谣,但是现在这种消息登多了,国民党里有人就害怕,说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又说:“我们有的同志乱讲话,说孙夫人、廖夫人也有封建思想,一直守寡不嫁人。”父亲问他这些消息是听谁说的,他说是国民党上层分子。父亲劝他不要听信这些谣言,他不置可否,最后又提醒父亲少登工农运动的消息。父亲这才清楚,虽然开过了“五大”,陈独秀并没有改变他对农民运动的看法。
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大大鼓舞了各地的地主、土豪和劣绅,他们在农村由蠢蠢而动到大肆反扑:袭击农民协会,暗杀农运领袖,摧毁刚建立的农村自治政权。同时,他们又与蒋介石分子勾结,潜入武汉等城市,散布诬陷农民运动的各种谣言。到5月初,“工农运动过火”的议论又甚嚣尘上,闹得满城风雨。
5月间,父亲的办公桌上开始堆满各地农协寄来的关于农村反动势力的骚动和农协反击的消息和报道,其中土豪劣绅勾结地方军警对农民的血腥屠杀更是触目惊心。父亲将这些消息冠以一个总标题《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予以据实报道,并且写了社论《巩固后方》。社论说:“在武汉方面,不但要严厉镇压蒋逆潜派来汉捣乱的逆党,并须严密检举潜伏的反动分子。在湘鄂赣境内各县,应以敏捷的手腕铲除乡村的封建余孽、土豪劣绅,及团防等类的反动武装势力,只有把乡村封建势力根本铲除了以后,我们方能说后方的巩固确得了保障。”(《茅盾全集》15卷356页)然而革命的行动总是比反革命的行动慢半步。刚刚提出要“巩固后方”,5月13日夏斗寅的叛变就发生了,并在17日占领了武汉的南门汀泗桥。这次叛变虽然被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I临时编成的独立师在三天内就击溃了,但驻守汉口和汉阳的国民党何键部和李品仙部却按兵不动,这显示了一种不祥的预兆。果然夏斗寅刚被击溃,长沙就发生了“马日事变”,驻守长沙的许克祥独立团在21日夜里突然袭击了省党部、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等革命机关,夺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捣毁和查封了这些机关,并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成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屠杀。随后,他们封锁了长沙对外的一切消息,同时声称这只是与工人纠察队发生了一场误会与冲突,他们仍旧拥护武汉政府,只是反对共产党的过火行为。然而纸毕竟包不住火,到了6月中旬,长沙事件的真相逐渐透露出来,特别是湖南各团体请愿团的到达武汉,终于使真相大白。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不登这些消息,《汉口民国日报》则不顾阻挠,连续五天登载了湖南请愿团的长篇报告,父亲并为此连续撰写了四篇社论声援请愿团的斗争。在一篇题为《扑灭本省各属的白色恐怖》的社论中说:连日本省各属雪片也似的告急,都是声诉各县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摧毁党部、民众团体,残杀农民的哀史。这些反动大联合的残酷,真是有史以来所仅见;他们杀人如芟草,又挖眼拔舌刳肠割首,活埋火焚、,甚至以绳穿女同志乳房,驱之游街。……我们总还记得不久以前,因为本省各属一二县内稍稍惩办了几个土豪劣绅,反动派遂张皇其词,造谣煽惑,竟说是“赤色恐怖不得了”,而以耳代目者亦从而摇头日:“糟,糟!”但是“赤色恐怖”尚未经事实上的证明,白色恐怖却已成为不可掩之事实了!……我们须知湖北各属土豪劣绅土匪的大联合的蠢动不是偶发的事件,也不是“农民运动过火”所起的反响,,……而确是反动派摇撼武汉的大阴谋中的一部。……扑灭各属的白色恐怖,便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刻不容缓的工作!(《茅盾全集》15卷396、397页)不幸,父亲预言的“大阴谋”不久便成为事实,7月15日宁汉合流,汪精卫宣布“分共”,公开叛变了革命,向共产党举起了又一把屠刀。由于当时的共产党没有掌握枪杆子,扑灭白色恐怖也就成了个幻想。
6月底,父亲把母亲送上了回上海的轮船,因为母亲怀孕已七个月,留在武汉太危险了。父亲自己则在7月8日写完最后一篇社论《讨蒋与团结革命势力》后,向汪精卫递了辞呈,当天就与毛泽民一起转人了“地下”。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父亲在晚年曾谈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他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在当时并不一般地反对农民运动,他只是害怕农民运动的高涨会吓退国民党,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夭折。他不相信共产党能单独挑起国民革命的重担,他对共产党掌握枪杆子也持消极的态度,认为条件还不成熟,怕那样做会激化与国民党的矛盾。而那时在共产党内也确实存在“左倾幼稚病”,这些幼稚过火的行为虽在整个大局中只是局部问题,但对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显然是不利的。由于陈独秀在党内的威望,国民党左派又信任他,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支持他,这就使得他的右倾路线得以推行,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7月下旬,父亲奉中央之命从武汉赶到九江,准备去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但因交通阻断而滞留在庐山,最后不得不于8月中旬回到了上海。由于父亲已列人南京政府通缉的第一批共产党员的名单,只得隐匿在家中,杜绝了与外界的一切交往,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在这时候,为了养家糊口,父亲重新拿起笔,开始了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幻灭》、《动摇》、《追求》三个连续的中篇,即《蚀》三部曲,从此父亲中断了他的政治活动家生涯而彻底成为一个文学家。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