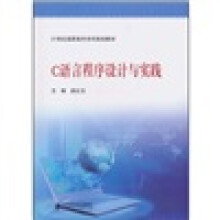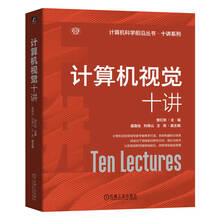郭沫若是近现代名人,这从他的各种头衔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头衔收录在《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典籍中。能将姓名作为词条载人权威典籍,这可不是靠月薪过日子的平头百姓能有的待遇,也不是只会两把刷子的舞文弄墨者可求的尊阶。
《辞海》里的词条是怎么写郭沫若的呢?是这么写的: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但《辞海》的这个写法,在专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里却又整成了这般说辞:“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仅此三项,再多,就没了,用词吝啬得像电报。
明眼人可能早已看出,这两本大书的说法不太一样。作为“社会权威”的《辞海》,明确说郭沫若是考古学家,而业内的学术权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却没说他是考古学家,起码没有明说他一定就是考古学家,这就叫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可见,郭沫若究竟是不是考古学家,有的说是,有的两说着,既不说’YES,也不说NO。《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这本大书是以考古学为书名并且是专写考古学的,收录了郭沫若作词条,却又不说郭沫若为考古学家,更叫人倍感蹊跷,不得定数。
但郭沫若在普通社会民众的认知里,却是赫赫有名的考古学家。记得我1978年考取吉林大学读了考古专业后,经常有行外的人听到我是学考古的,就告诉我说,那你们的祖师爷可是郭沫若啊!足见在公众的话语里,郭沫若不但是考古学家,还是考古学家的祖师爷呢。
那么,考古方面的专业人士又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我找到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夏鼐在郭沫若逝世后写过的一篇纪念文章,那文章发表在专业杂志《考古》上,里边有这么一段话:“郭老虽不是一位田野考古工作者,但是由于重视田野考古工作,对这工作也感到兴趣。”我还翻到了曾创建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后来也曾担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在《如何使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一文里说过的话:“亲自参加,或至少熟悉田野工作,早已成为考古工作者的一个必要条件了。
”夏鼐和苏秉琦是公认的考古大家、学界翘楚、新中国考古学的开创者和引领人,由他们从考古专业的角度来评述,该算够权威了,即便作为盖棺定论,也不过分,那就是:郭沫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家,起码不是以田野考古为职业的考古学家。
所谓田野考古这种工作,在考古界内的重要地位,可用“定尺”、“天条”来比喻。换句话说,这也是考古学之所以有别于古物学或金石学而成为一门近代科学的关键之一。众所周知,在考古学作为近代科学诞生以前,国外早就有了古物学,中国可能更早些,至少在宋代就有了收藏和著录古物的金石学,也就是专挑有文字铸刻的那些铜器和石刻来把玩和鉴赏,以实现“证经补史”的目的。至于国外的古物学,远的不说,18世纪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就带着研究埃及的学者同行,在埃及寻访古迹和古物。他甚至还劫掠过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古物,作为战利品带回法国,建立博物馆。拿破仑曾经有句名言传世,那就是“让学者和驴子走在中间”。在他的远征中对学者和驴子都格外保护,因为学者中有博物学家,能认识古迹和古物,而驴子不但能驮去成百箱的武器和辎重,还可以把劫掠到的珍贵文物带回法国。对这类也是在野外所做的各种调查和挖掘,我们既不能承认拿破仑带领的博物学者是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家,更不能贴标签式地认定拿破仑就是考古学的领导者。否则,那笑话就闹大了。
再看中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有过三次文物大发现:一次是1899年,比较流行的一说是,相当于今天教育部最高官员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一味叫做龙骨的中药材上发现了刻在上面的文字;一次是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篆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4万多件,后来遭到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一批又一批外国人乃至中国不少官吏的劫掠;还有一次是在1901年前后开始的被王国维称之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之一的“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即著名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以及楼兰、尼雅等地发现的汉简。以上这些轰动世界的文物发现,都离不开野外作业,但如果哪位说这些就是考古发现,进而推演这些人都可在考古学家之百年殿堂上荣列一个牌位了,恐怕稍有点考古常识的人都不会答应。何况,中国的考古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一般业界认可的标志,是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正式考古发掘。换言之,这些带有劫掠、探险、寻宝目的的行为以及取得资料的手法,最多只能说是文物发现而已,都不能和后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与科学方法相提并论。
文物发现与考古发现的性质不同,方法有别,目的迥异,喜欢考古和以考古为职业也是两码事,不能随便放在一个锅里煮。这要展开来说,起码涉及两步解法。
第一步,是看平时的工作是不是多在野外,说白了也就是是不是以发现遗存为主要职业目标。活忙的时候,一年到头在城里呆不了几天,虽不至于像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到了年根儿底下才回家,过了正月十五又下了工地,都是常事,都是常态。像我有个大学同窗叫魏坚的,据说常年都是在内蒙古的考古工地上,一干就是300天朝上,而且还兴致勃勃,乐此不疲,来劲得很。我虽然不知道他这种“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考古汉子在考古中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倒是真佩服他太太是怎么拉扯孩子而又保留他户籍的。开句玩笑话,像他这种人早就该被起诉,判他个考古犯,每年在家关押3个月再放出来,才算对得起家人。考古连年累月,就意味着背井离家。不知何时起,这首顺口溜就在考古圈子里流传着:“嫁人不嫁考古郎,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来,带回一堆臭衣裳。”一届传一届,一辈传一辈,离校时,好涂鸦的毕业生就信手把它题在寝室墙上。家人们也经常把它调侃式地写进两地书,你像有位考古太太就曾揶揄自己丈夫的职业道:“远看像挖土的,近看是挖墓的,原来是考古的。”考古是与家人别离,却又和古人相聚的活计。吉林大学有一位年轻的考古老师叫方启,他不无感慨地透露过些许类似的感触。他说,考古人“最难受的是对家人的愧疚——笔者结婚1个月就出差田野调查,媳妇每次打电话都说挺好挺好的,突然有一天就放声大哭。她笑言:嫁一个考古人就要学会坚强。这样的经历在考古圈中是家常便饭”。
第二步,就是看你会不会挖。所谓会不会挖,就是能不能按照考古行业的操作规程要求来把工地做好。做好的标准,不是看你挖到了什么,要紧的是看你怎么挖的,挖得科学不科学,专业不专业,行家不行家。有一次,全国召开各地考古成果汇报会,某个省的老兄一个劲儿地介绍他们挖了多少多少墓葬,墓里出土了什么什么器物、有多么多么珍贵。但见他兴高采烈拉着粘纸单子,全然像个收租回来的报账先生。只听得主持会议的夏鼐干脆叫停,批评道:这又不是献宝大会,你还是讲讲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些遗存的吧,发掘时遇到过什么问题,又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见,考古发现了什么并不重要,怎么发现的才尤其重要,知道了这一点极其重要,不知道这一点非常糟糕。用前故宫博物院院长、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的话说,就是看在同样的面积或空间里,谁能挖到可供复原历史的信息最多。而不是只拣选完整的器物,不要残片;也不是虽拣残片,但不要人骨;更不是也拣人骨,但不要动物残骸等。一句话,凡是对复原古代人类生活及其生存环境有用的都要收集,都不能丢弃,“弃骨取器”,行业大忌。否则,一通乱刨,只顾挖宝,专拣值钱的玩意掏,那就是破坏,那就是比盗墓贼还坏。我有个搞博物馆陈列设计的朋友,常常讽刺我:“你们考古的,除了会挖,还会干什么?”他这话叫我郁闷,却道出了一个真谛,那就是:会挖,才是考古人的看家本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