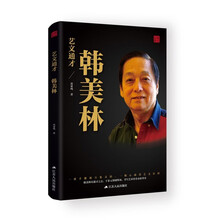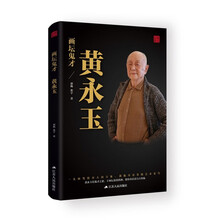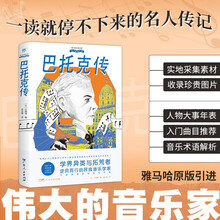小时候
我是山东人,从小生长在江苏省南通县。我在那里读完小学和中学,后来才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当时南通号称文化城,因为当地有一个著名的绅士——张謇,他是清朝末代状元,是个改良主义者,主张实业救国。他在南通家乡开设了很大的纱厂,当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的时候,这个纱厂赚了不少钱。张謇便利用他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为家乡办了一些事情:修建了一条马路,城里接上了电灯,也办了一些学校,如农学院、医学院和研究戏曲的伶工学校等。他喜欢书画和工艺美术,因此南通城里的公园、楼台亭阁、假山石和仿效西湖苏堤、白堤桃红夹绿柳的两道长堤都修筑得十分美观大方。他还精心创建了一个博物院。我的父亲在北洋军阀时期做过营长,后来开办电影院做经理。我小时候,母亲看我嘴唇皮薄会说话,说我长大了可以做律师。我父亲喜欢赋诗饮酒、古玩字画,他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磨墨写字,还让我大哥带我回山东老家,登了泰山,我竟然画起泰山的景色了。我八岁学拳术,十八般武艺全都学了点。拳术的步伐、体态以及呼吸和力量的运用,都对我以后演戏帮助不小。那时候认为没出息的人才去演戏,演戏的人被称为“戏子”,地位很低,我的父母自然不会让我去学戏,我也没想到我以后却一辈子就干了演戏这个行当。
张謇是南通的望族,他家每年庆祝寿诞喜庆吉日,便邀请北京和上海京剧界的名角到南通去演“堂会”。当时京剧界的文武昆乱济济一堂,梅兰芳、欧阳予倩、程砚秋、余叔岩、王凤卿、杨小楼、郝寿臣、王长林等都到过南通,可谓盛极一时。名角同台合演,更是机会难得。我因为父亲的关系,有机会恭逢其盛,看了一些精彩的演出。那时候,我常常喜欢溜到后台去玩。有一次,我正站在上场门偷看场子里的情况,忽然背后“哗”的一声喊,吓了我一跳,急忙让开,只见好大一个“张飞”连声喊着“哇呀呀”,朝后退了几步,然后“噔、噔、噔”冲上台去,好似猛虎出山一般。后来我知道这叫做“上场风”。这个“上场风”对于演员出场亮相很关重要,他如果不退后几步再出场就显得没有力量,没有气势。
又有一次,我在后台看关公戏《走麦城》。演员们早就化好了妆,穿戴整齐,焚香静坐,鸦雀无声,给人一种肃穆神秘的气氛。那演关公的演员紧闭双目,在那儿运气养神。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懂得,这当然是一种迷信,但也未尝不是京剧演员进入角色培养情绪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次,我在后台看见一个当时南通挂头牌、名叫张德禄的武生,他在台上大概出了点差错,刚下场,他的师父拿着很粗的棍子直朝他浑身上下抽打。这样一位在台上顶天立地的赵子龙,到后台却被打得如此凄惨,这在我童年的心灵里感到一种奇异的痛楚。这时候我也知道吃“演戏”这碗饭可不简单。以上三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没出息
谁都有他的童年,小孩子也最爱学大人的样子。我第一次演戏是在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举行了一次家庭演出晚会。我做了戏票,“卖”给妈妈和姨妈,要她们凭票入座,像真是上戏院看戏似的。演出的剧目是京剧《空城计》。我演诸葛亮,我的表兄演司马懿,我们为了“隆重”起见,还化了妆。司马懿是白脸,可我表兄脸上有麻子,我就异想天开约着表兄半夜里溜到南城门口,从张贴的广告纸上偷偷地刮下了点金粉末,第二天在我表兄脸上抹了个金脸,又把拍蚊蝇的“蝇掸子”做髯口,我们就这样粉墨登场了。当我们正演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回来了,我们怕他责骂,赶快卸妆洗脸。我父亲每次回家我表兄总要给他沏茶陪着说会儿话,这次因为匆匆忙忙没能把脸洗干净,他脸上麻坑里还留下了不少金粉,于是,我们串戏的事情就此“穿包”了。虽然我父亲并未认真地责骂我们(大概是春节里的缘故吧),但却也白了我俩一眼,又随口说了一句:“没出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