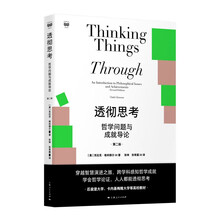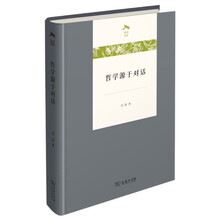奥托生活在经院哲学初步繁荣的时代,与以前几个世纪相比,经院哲学家对思辨、对理性的更多的强调和重视对奥托无疑有深刻的影响,更何况他还是德意志皇族的一员。这些因素都使奥托在比奥古斯丁更大的程度上肯定世俗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奥托时代的基督教会已成为一个现实的、凌驾于各国君主之上的权力中心,远非奥古斯丁时代的国教地位所能比拟,这种现实在奥托的历史神学中的反映就是上帝之国与教会的进一步等同。两种显然对立的倾向同时出现在这位思想家的观点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痛苦的矛盾。如何解决或者调和这一矛盾,也就成为奥托给后世提出的课题。
梅里斯认为:“中世纪缔造了历史哲学的三大形态。奥古斯丁处于开端,他给予中世纪历史哲学以典型的形式。弗勒辛的奥托意味着中世纪世界观的顶峰,托马斯·阿奎那和但丁意味着中世纪哲学的重要的结束语。”而这个结束语的特征也恰恰就表现为教会和国家关系的和解。
事实上,托马斯·阿奎那并无意于建立一种历史哲学。然而,他依据亚里士多德哲学所建立起的那个无所不包的宗教哲学体系,却为新的历史哲学思想的产生扫清了道路。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等级制中,一切存在被划分成两个大的体系,即感性的现实和超感性的现实,或日自然的王国与神恩的王国。而人的灵魂正是这两个王国的衔接部。作为分离的形式它向往超感性世界,而作为内在的形式,作为生命的力量,它又转向感性世界。人同时是这两个世界的公民。而在尘世中,与感性世界相应的人类组织是帝国,与超感性世界相对应的是教会。人也可以同时是帝国和教会的成员。于是,国家不再被纯粹看作是恶的代表,不再与上帝之国处于尖锐的对立中。虽然国家仍没有绝对的价值,但至少已有相对的价值,在上帝的救世计划中履行一定的使命,是神恩的救世道路上的一站。
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其历史哲学思想正是从托马斯·阿奎那的上述观点出发的。在但丁看来,统一是人类的本性,是人类所分有的神性,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由于上帝的本性是统一,上帝所创造的人类也就分有了上帝的这种本性。但是,由于人类的始祖对上帝犯了罪,这种原初的统一也就被打破了。既然人的存在目的就是回归上帝,因此,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也就是重建这种统一,这也是上帝的意旨所要求的。“人类只有尽其所能与上帝相像,才能处于最佳状态,而人类又只有达到完全统一才接近上帝的形象,因为统一的真正基础就是上帝本身。”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但丁和奥古斯丁之间也就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但与奥古斯丁不同,但丁认为,作为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作为上帝的意旨的统一既具有伦理、宗教的性质,也具有政治、社会的性质,因而也就包含着两种统一形式,即教会和世界帝国。梅里斯认为:“相对于奥古斯丁和弗勒辛的奥托的历史图像,但丁的历史哲学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巨大的进步,这首先是因为,宗教对他来说已不再被看作是唯一的上帝之子,而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文化力量,特别是帝国,相对于教会取得了一种独立的价值意义。”教会和帝国都是人类统一这个终极目的的暂时性实现,都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都是直接受权于上帝。教会是所有精神事务的绝对统治者,是道德和宗教事务的最高仲裁,帝国则是世俗事务的绝对统治者,是尘世的最高权威。二者具有同等的权力,只有二者完全分离、互不干涉,上帝的意旨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世界历史也就是这两种力量分而治之的历史,而历史的终极目的则是文化借助帝国和教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最终建立一个和平的统一国度,这也就是上帝之国的实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