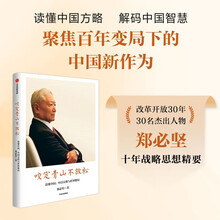双方的表述又需要面对不同的问题。如果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的问题来自历史,即:他们难以回答如果抽去他们认为“让子孙后代脸红的”红色中国历史,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如何完成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这一历史根本问题;那么新左派面对的问题则来自当下,即:他们难以回避今天“唱红歌”活动作为一个“追忆仪式”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红歌”在其所产生兴起历史中的意义这一事实。
当中国共产党已经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整个社会资源运作和分配模式已发生巨大转型,社会分层日益明晰,革命时代所追求并初步建立的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倡导“唱红歌”,一方面体现出对红色中国历史的定位和评价,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移花接木式的意识形态征用,将本来源自于革命政党领导的反抗与斗争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移用为执政党对现存社会的维护与发展之力。这一点,与新左派“回到过去”的激进要求,在对未来发展模式的构想上,纵使可以不乏重合之处,但终究还是有着很大分歧的。更无论在今天环境中,那些关于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解放自己去奋斗牺牲的歌曲内容,或许还沉淀着艺术上的感染力与仪式上的神圣性,但确已不如其产生兴起之初,能作为一个时代的历史共识了。因此,正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讲述荒诞的“唱红歌”故事时,回避了“红歌”携带的历史记忆在民间所能获得的认同感;新左派则在讲述一个个热情的肯定“红歌”故事时,回避了“红歌”在今天的被征用、被组织事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