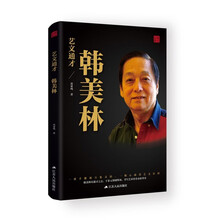故我依然
一九二五年我出生在一个温馨而自在的家庭。父亲是总工程师。我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我母亲是姐姐们的继母——这关系可是在我九岁丧父之后,两个姐姐帮着撑持家庭并且把我这个丑丫头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我从亲戚、邻居夸我姐姐的话里才知道的。我总觉得我们家无所谓“家教”。我爸爸活着的时候老没大没小地撺掇着我们上树、爬墙,还拿他当大马骑,并常年在戏园子里订包厢带全家看戏,孩子们在学校里开同乐会演戏、演讲、跳绳……爸爸都是最佳观众“追孩族”。父母从没说过一句让我们好好读书的话,却一个书库、一个书库地给我们买书:《万有文库》、《中学生文库》、《小朋友文库》……连描金漆绿题字的玻璃橱门的书架子一起买回来(真格的,现在讲究高消费了,倒连买个书架也费劲了)。姐妹兄弟办起了“我们的图书馆”,还刻了章。我最喜欢整理书架,把书摊一地,慢悠悠半懂不懂地一本本看过去。爸爸留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我们家从北京带到青岛去的王厨子患败血症暴卒于医院,爸爸说他是为我们家死的,出大殡时爸爸披麻打幡,我们全家白衣送丧厚葬于当地德国公墓。
谁善待过我们家,我们都不会忘记,虽说俗礼答谢修书叩安这一套总记不得。
“七岁看大”这句话对我不是没道理的。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儿。大哥宗江把痴迷于戏剧艺术的圈给我套上,妹子我也受下了。其实,一九四0年我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只因我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我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我梦着去当护士,母亲说当护士太苦了;我梦着去当文书,因为家里有英文打字机,我会打,可人家嫌我小;梦见卖花,因为“小小姑娘清早起来,提着花篮上市场”的歌儿好听;梦见吆喝着卖菜、摇拨浪鼓卖针头线脑……反正自始至终没做过当巨星、当文豪的梦。
也许我此生没得到发展的天赋是当个好主妇。十来岁时,入冬课余要做五双棉鞋帮,织五副手套、袜子,把五件毛衣拆洗更新加大。我干什么活儿都挺认真,和我猛然间被推上话剧舞台以及又演电影一样——分内的事我必得做好;分外的、搭不上手的我也尽力试着去做。无论是多幕剧落幕之前我上场演一个不说话的新娘子,还是第一幕幕启时演个走场子边的民女,我都早早化好妆候场并守到谢幕。一九五九年我奉命专业创作,不坐班。自忖不坐班等于全天上班,自此除了三伏天我从来就不穿拖鞋了。也许是我又把演好角色写出文章当紧针密线缝鞋帮了。是的,我此生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女儿、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而此一角色却在个人际遇、民族兴亡中衍化出种种情节。文法须知:情节者性格之历史也。删略情节种种,堪慰故我依然。
其实,我一生中迂回曲折最“出戏”的情节,是“难为赵丹妻”。
一九四六年我开始拍电影,一九四七年我碰到赵丹,一九四八年我们结婚。主要因为他是个落拓不羁、饱经摧残、乏人照料的有正义感的单身中年艺术家。他的锐敏和正义感注定了他一辈子不得安宁。七十年代后期他曾为邓拓写过挽联:
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
瞻望未来万种艰难犹有牺牲
岂料终成了谶语。我既然钟情于他的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载身为赵丹之妻,敲打得我也就不仅仅是“陪斗”的了。
前两年我重病住院(至今“保外观察”),为此我哥哥弟弟,曾围坐叹息掉泪说:“如今我们不愁儿、不愁女,更不愁自己,就愁小妹(姐)了。”谁都说我命苦,认得的不认得的人常劝我:“想开点。”大哥叮嘱我常记一句祷词:“Take it easy”(随它去)。我真算想得开的了。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老师命题写有关过年的作文。同学们写欢欢乐乐,我写父亲遗像前的一对白烛。彼时从来自拟是“天下惆怅女”,把个“葬花词”、“祭妹文”默写得跟金刚经似的。往后年复一年,净轮到我碰上些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都没的悲剧情节,我便愈来愈无绪去愁了。劳劳尘世,如今倒数秒不知从哪个寿数往回磨蹭,于是给自己定下个天晓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则:
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
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
诚然,一个人干什么都受生存环境和时代潮流的影响。而不干什么,则是理性的选择。归隐书林,还我本原,“勤习针黹”,是此时此际我的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