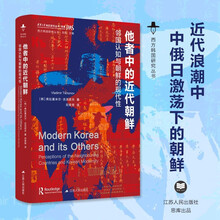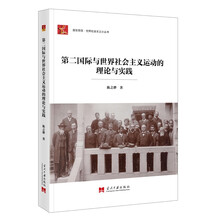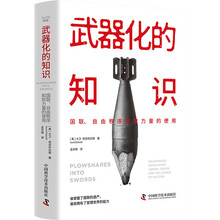其次,作为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 Labrousse)的门生,丹尼尔·罗什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功底运用于文化场,同时摒弃芒德鲁(R Mandrou)所倡导的思想史的综合分析方法。1970年代,他将调查研究的对象扩大到知识性著作、各类藏书、书籍的历史、游记和书信,丰富了实地调查法的内容。他拓展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始终把奠定新的方法论基础作为自己的一贯愿望,因而他不拘泥于文化共和国关于古典历史学的各种约束,很早就开始发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1993年出版的《启蒙运动中的法国》是丹尼尔·罗什对历史学方法论的 又一次贡献。作者勇于挑战学术前沿,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中吸取灵感,深入发掘研究主题,对历史时段进行大胆的分割。
地毯编织工人西蒙(Simon)的自传为我们重建了曼恩省(Maine)的生活情境。他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来叙述订婚,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母的影响与年轻人的自由是如何达到平衡的。路易·西蒙和安娜·尚波(Anne Champeau)以第一人称的笔触和非常独特的手法再现了这一幕:对于她来说,那是一见钟情,应该尽快在教区的结婚记录簿上登记;而对于他,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遵循非常明确的惯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这期间并不排除发生激烈的冲突。温馨的爱情空间建立起来,幸福在两个家庭之间荡漾,在富于田园气息的高级餐馆,以及情侣们经常约会的墓地、年轻人的节日盛会、夜总会等方圆5到10公里的土地上蔓延。这一类的剧本一般都没有安排情敌的介入以导致乡村爱情的失败,因而都是很“大路”的手笔。
如果走出家庭进入国家的范畴来思考,我们就可以得出此类移动的规律。在旺多姆瓦(Vend6mois),在位于佩尔什(Perche)到博斯之间的地方,J·瓦索尔(J.Vassort)分析了大约3000份结婚证书,从中得出了明确的结论:35%的新郎和仅8%的新娘结婚时不居住在堂区。人们很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些位于边境的堂区并且进入这个圈子,但是一项人口统计资料分析显示,由于婚姻关系而引起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移动构成了一种更为确定的移动类型。首先,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大范围的移动,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10%的男性出生于旺多姆瓦以外的其他地方,其中4%到5%超出了法国大革命时期邻省的边界,距离远达20到50古里;女性的这两项比例则分别下降到4%和1%以下。这种迁移的地理学意义来自于他们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地位:27%的显贵,69%的军人,手工业者和工薪者占20%到26%,农村人的总数还不到10%。这是一场劳动力的大迁移,他们来自法国西部拥有草地绿篱的地方,为边境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必不可少的短工。
这样的移动不能当作“浪费时间”来体验,而应该把它看作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它可以无穷变幻。塞巴斯蒂安·梅西耶(Sebastien Mercier)阐明了各种社会变化,因而对此很有感触:专属于富人的速度、劳动者的一贯迟钝、对于溜达的一致偏好。他揭示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子,吸引的圈子和排斥的圈子。从家庭开始,这些圈子就安排着空间的惯例和实践。房屋,从简陋的茅屋到富人公寓,是与第一个圈子相对应的:属于家庭的、灶台的、熟人的、让人安心的那个圈子。超出这个圈子,凝聚力就减弱了,彼此的了解就更复杂也更困难了。关系网可以遍及乡村团体,遍及全国。在认识的与不认识的人之间,在熟人与陌生人之间,时刻存在着一种对立。随着空间的扩大,社会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规则、监督、习俗取代了基本出于本能的自由,取代了性格上的冲突。规则、监督和习俗来自于机构(教会、教堂财产管理委员会),来自于当权者(大法官、领主)。简言之,权力代替了影响力。经济关系甚至也发生了改变,无偿的领域也都设立了账簿。在农村,家庭圈子的概念将狭义的或者相对广义的家庭与开发经营、社会单元(甚至税收)、生产单位等同为一。这类似于城市的大多数阶层,在他们的生活中,“家庭温暖”是百姓生活的一个要素,18世纪的巴黎便是如此。作为传统的人口统计学,这种可能为生活的不确定性所打破的基本构架,就是在上代与下代的关系中造成本质上不连贯的一个因素。社会经济对于“脆弱生活”的压迫(在城市或许比在乡村更为严重)仍然是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基于此,婚姻关系和经济关系成为了两种主要的紧张关系,并且构成了空间必须扩大的理由。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