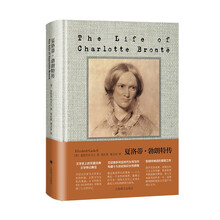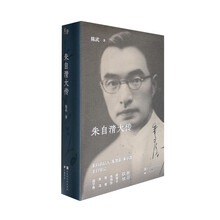02 你的母亲是樱桃 我的母亲是血泪
关于海子的生辰,我在《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4月出版)和《海子评传》修订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中都这样写到:“海子:1964年2月19日出生于前边所描述的查湾。这个日期作为最基?的个人资料,标明在他的身份证上。但据其父亲介绍,这却是一个以农历记时的日期,也是早先的农村人常规性的生日记时方式。这样,海子的出生日期若以我国户籍档案制度规定的公历来记,当是1964年4月1日。”这个说法,我当然认为就是铁的事实。但在此后相继出现的有关海子研究的出版物上,对这个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在同一个作者的笔下竟相互矛盾。比如在余徐刚的《海子传》中(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其封面勒口处关于海子的介绍为:“1964年5月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查湾”,但在该书的末尾却是这样的表述:“1989年3月26日,?天是海子的公历生日。一大早……”对于这一矛盾的表述,我在书写《海子评传》修订本时并未特别在意,因为这部《海子传》几乎是一种接近小说的写法,并且其中众多的原始材料和理论分析原文,都来自我的《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而作者却尽力把它们模糊成自己的原创。因此,对于这部《海子传》中的诸多表述,我觉得既不必特别当真,也不必特别计较。但是,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说法呢?他们的根据又是什么?
在对这部书做第二次修订的此刻,也就是2010年11月12日傍晚,我拨打了查湾海子父母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查振全老人。当我再次核对这个问题时,查振全的回答却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海子的生日是1964年农历2月11日。这件事,海子的母亲在去年县里办的诗歌朗诵会上,当着众人的面专门做了说明。我问:那么,海子身份证上的时间是怎么来的,他自己还不清楚吗?答曰:海子这小子他记混了。
所谓“去年县里办的诗歌朗诵会”,是2009年3月26日,在海子去世20周年时,由怀宁县委宣传部举办的“中国·海子诗歌研讨会”。研讨会前我接到了邀请,其间海子的二弟查训成又数番电话催促,但我终因其他琐事未能成行。?海子的母亲在由官方首次举办的这个研讨会上特别说明此事,显然也曾多次遇到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询问,故而在这个官方举办的研讨会上,做出这一郑重其事的权威发布。毫无疑问,一个人生日最可靠的知情者,并不是他本人,而只能是他的母亲。
那么,海子的生日按公历来记,便是1964年3月24日。
到此为至,我想这个问题将从此不再成为问题。
海子的父亲查振全1933年生人,其母操采菊小其父两岁。这样算来,海子出生时,其父已3l岁,可以称得上是中年得子。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其实在海子出生之前,查振全夫妇还曾生育过两个女孩。其中老大长到两岁时,因疾病缠身而夭折;之后的老二更是短命,出生仅一天后便离开了人间。这样的境况,对查振全夫妇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但自从海子这个男丁出生后,却鬼使神差般地顶住了查家的这一颓势。非但如此,查家的人丁竟以此为转折由衰而盛。随之,海子的三个弟弟相继出生,头碰头的四个男丁,与父母合成了六口之家。对此,笔者没有相关的理论予以解释,但农村人对这种现象却有一个现成的说法,这就是这个孩子的命硬,和家族中的人命中犯克,而家族中亲属们的精气,遂独聚于这个孩子一身。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不知道。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类似于这种神秘主义的结论,却是来自对无数现象和规律的总结。
儿时的海子肯定不是一个神童,但却的确具有良好的天资。查振全夫妇都是约略能识得些文字的人。据海子的母亲操采菊老人讲,当年家中时而有从亲朋邻里处借来的一些杂志画报,她得闲时便常一边翻看着,一边为身边的海子“讲书”。记得大约是在海子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她为海子讲完书后,海子第二天拿着那本《安徽文学》杂志,给她指着封面上刊名的第一个字,说这是一个“安”字。
这似乎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一个儿童对于陌生事物的好奇,人类都有的炫耀心理以及在大人跟前获得赞赏的满足,都会成为个人潜能开发的某种动因。而操采菊在自己六十四岁的年龄上,仍能对儿子童年的这一表现记忆如昨,实则透露了她自己的青年时代,那种浮动在内心终而又被沉重的生活消磨了的、对予文化和由此打开的广阔世界的向往。这是一位首次见面便能使人心头蓦然一紧的老人。她平静、茫然、浮着一层雾翳的眼睛,一霎间会让人感受到那种艰辛生活在一个农村妇女心理上的叠压,尤其是失去爱子巨大的打击,使她十年来仍走不出那一疼痛。老人身材不高,本来紧凑精干的身型因着这一精神变故,而似乎负着一重拖累。见面之后刚听完同行者的介绍,她便拉着我的手微微抖索着,并仰起脸端详了良久,似乎要在我的面部找到海子在另外一个世界活着的见证。这一瞬间,我能强烈地感觉到她内心的亮堂,她知道那另外一个海子活着的世界——在距离查湾一个小时汽车路程的安庆城,在安庆以北上百公里的合肥,在合肥以北更远更大的北京,也在这个国度所有对诗歌和文化怀有理想与热情的、那些文化艺术人生活着的地方——她知道,自己的儿子一直是那一广大群体中的在场者。
而这些人,又偏偏都不在查湾,也不在他们的高河镇。
当老人在我的面部获得了某种信息后,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一看见你们我就心里发痛。”眼睛便随之潮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