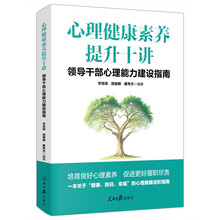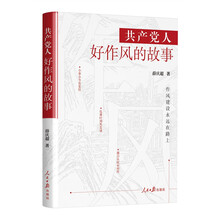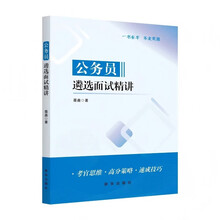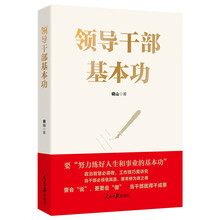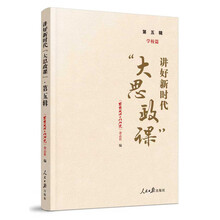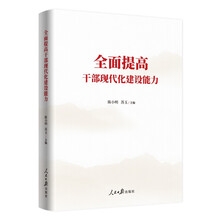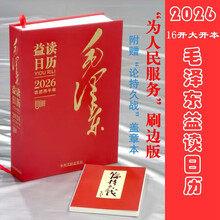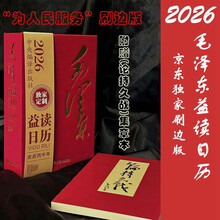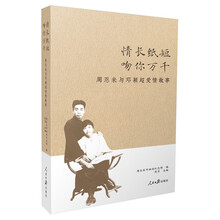唐代以直笔修史著称的史家吴兢,在他编著呈给唐中宗、玄宗御览的《贞观政要》中,对唐太宗的政绩论述颇详。《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一开始便记述了唐太宗常思“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君道明言。谈及政体,太宗指出:“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用舟与水、根与枝叶来定位君民、国家与百姓的关系,足见唐太宗的民本思想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直接动因正是总结强盛的隋朝滥用民力、短命而亡的历史。唐太宗曾多次谈及炀帝轻用民力的危害。贞观二年,太宗说:“卿等岂不见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朕每念及于斯,未尝不忘寝辍食,所以师古作法,不敢任情。”可见唐太宗对此段历史的感受何等之深。
唐太宗的虚怀纳谏是历代封建帝王无法比拟的,其实这也是他读史用史的具体表现。唐太宗之所以能倾听逆耳忠言,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目睹了由于隋炀帝刚愎拒谏而招致隋朝灭亡的结局。史称:“隋炀帝骄矜自负,以为尧舜莫己若,而讳之憎谏,乃日‘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新唐书·吴兢传》)唐太宗通过读史了解到隋炀帝独断专行酿成的种种恶果,他曾明确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唐太宗以前朝隋炀帝为反面教材,从“憎谏”转变为“求谏”,从“臣下钳口”转变为谏臣满朝,从上下壅隔转变为上情下达。在这一点上毋宁说,没有隋炀帝就不会有唐太宗。
贞观年间,君臣经常探讨历史上各王朝更替的原因,用史引为警惕,成为佳话,这是形成大唐盛世的原因之一。
同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相联系的,是贞观年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修史盛况。他在位期间,确定了官修史书和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也就是政府出资设史馆组织修史和由政府首脑宰相来牵头负责。修史的目的十分明确,即“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为治国之需服务。最初史馆因隋之旧隶属于秘书省,后移史馆于门下省,由宰相亲自主持。共用三十年的时间,官修正史八部:《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史》,占了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唐太宗还亲自为《晋书》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传论,是历史上唯一由皇帝亲自写史论的一部史书,因而《晋书》旧本题为“御撰”。
除了重视编撰前代的历史外,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当代历史的编著。贞观年间的当代史包括国史、实录和起居注三种体裁。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对历代帝王不亲看国史的做法不理解。他在贞观十四年(640年)说,不知为什么国史不让当代的帝王看呢?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回答说:“国史善恶均书,国君哪会没有缺点,史官怕犯忤逆,故不能让国君看到。”太宗说:“我的看法与古人不同,现在我要看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你们完全可以呈上来。”
房玄龄主持下将国史删减,写成编年的实录,唐高祖、太宗各二十卷,于贞观十七年呈给太宗,这是唐初的第一部实录。太宗表彰和赏赐了房玄龄与执笔修撰的史官许敬宗。太宗认为实录中对玄武门之变的史实“语多微隐”不妥。他指出,玄武门之变与“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存”一样,应不讳经过,“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唐太宗也很重视帝王起居注的编写。贞观初,设起居郎。贞观十五年,近臣褚遂良由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详记唐太宗的言行。翌年,太宗问褚遂良说:“你知道起居注的内容,我可看否?”褚答:“善恶全记,使君主不敢为非,但没听说过要给皇上看。”太宗又问:“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记下了吗?”褚答:“不敢不记。”太宗说:“应该这样。”
秉笔直书这一史学原则,在贞观年间是太宗与史官们的共识,大体也被贯彻执行着,应当讲中国史学的直笔传统在唐初得以发扬光大。
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在中国历史上拥有杰出的政绩,受人景仰,究其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是唐太宗读史、用史、以史为鉴,能虚怀纳谏,因而他拥有清晰的智慧、开阔的视野、宽厚的胸襟和缜密的决策,才创造出“贞观之治”的盛世。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