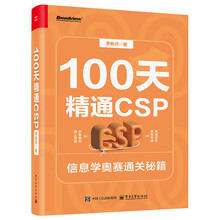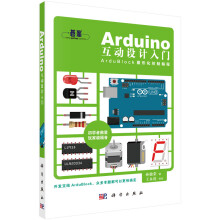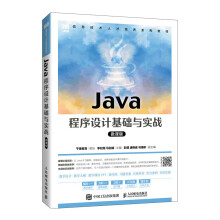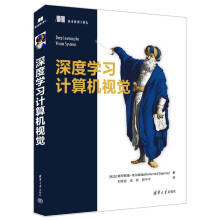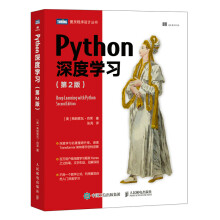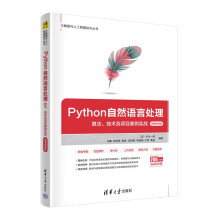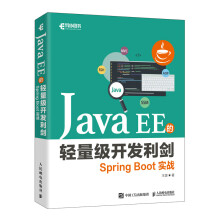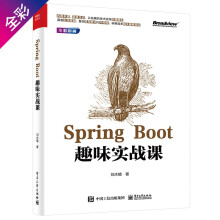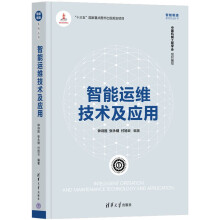当然,对于中国的区域研究或者地方史研究,并不是从郝若贝这里才开始的,而是早在施坚雅(william skinner)那里已经开端。施坚雅在他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非常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不过,在中国史领域里,这种具有明确方法意识和观念意识的研究风气,却是从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才开始“蔚为大观”的。公平地说,本来,这应当是历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研究确实在很长时间里忽略地方差异性而强调了整体同一性,这种研究的好处,一是明确了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二是凸现了不同区域、不同位置的士绅或精英在立场与观念上的微妙区别,三是充分考虑了家族、宗教、风俗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比如,近来包弼德提出的超越行政区划,重视宗教信仰、市场流通、家族以及婚姻三种“关系”构成的空间网络,使这种超区域的区域研究更吻合当时的实际社会情况。
这一区域研究方法,在日本学术界同样很兴盛,不止是宋史,在明清以及近代史中,也同样得到广泛使用,领域也在扩大,除了众所周知的斯波义信在施坚雅书中关于宁波的研究,以及此后关于江南经济史的研究外,在思想史、文化史以及社会史研究中,也同样有相当的呼应,这一类研究成果相当多,正如日本学者冈元司所说的那样,尤其是1990年以后的日本中国学界,对于“地域”的研究兴趣在明显增长,这种区域的观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细化了过去笼统的研究。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