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伦敦回来已经有一个礼拜了,此时我正坐在前妻以前的庄园——斯坦诺普庄园——那座小门房里的餐厅的餐桌旁,费劲地整理着10年前我寄存在这里的那些旧文件、家庭照片和信件。
自从我和苏珊离婚后,我实现了自己一直以来盼望的一个梦想:我驾着一艘46英尺长的摩根型双桅船——我称之为“波玛诺克二号”——花费3年的时间做了一次世界环游。顺便说一下,“波玛诺克”是本地印第安人对长岛的称呼。我那位杰出的祖先、长岛的本土居民沃尔特·惠特曼先生经常在他的诗歌里使用这个词——如果沃尔特大叔有一艘46英尺长的游艇的话,我敢肯定他会把它命名为“波玛诺克号”,而不会是“我听到美国在歌唱”——这个名字刻在船尾显得有点长了,当然也不会是“草叶集”,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跟航海没多大关系。
我航行的最后一站是英国的伯恩茅斯,三个世纪以前,萨特家族的那些先辈们就是从这里扬帆远航,驶向美国。
冬天就要到了,我彻底厌倦了海上生活,口袋里的钱也不多了,再加上我的旅游癖也得到了满足,于是我便以一半的价格卖掉了那艘船,然后去伦敦找工作。最终,我和一家需要一位美国税务律师的英国法律事务所签了约。在成为波玛诺克二号船长之前,我就是干这个的。
我把几张苏珊的照片铺在餐桌上,在树形吊灯的灯光下一张张看着。苏珊以前是——现在也许依然是——个漂亮女人:她有一头红色的长发、一双勾人心魄的绿眼睛、一对微微翘起的嘴唇和一副只有骑手才有的完美身材。
我拿起一张照片。照片里,苏珊坐在我第一艘船,也就是原来的那艘波玛诺克号上。那是一艘36英尺的摩根型帆船,我很喜欢它,但最终我宁愿在牡蛎湾港把它凿沉,也不愿政府拿它去抵押我拖欠的税款。我想,这张照片可能是1990年夏天在长岛海峡的某个地方拍摄的。照片上显示那天的天气很好。苏珊站在甲板上,一只手捂着下身那火红的丛林,另一只手则捂在一只乳房上。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吃惊的表情,既带着一丝挑逗,又有些许害羞。
那是苏珊在野外表演性剧的场景之一。我记得我是从一只爱斯基摩人用的皮船爬到游艇上,发现船上只有她一个人,并且还一丝不挂,于是便让她做了我的性奴。
这个女人不但有一副绝佳的身材,想象力也是一流,并且性欲十分旺盛。说到性爱场景剧,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婚姻之火继续燃烧。它的效果十分明显,因为20年来我们俩都没有对对方不忠。至少可以这么理解,直到一位新演员——弗兰克·贝拉罗萨先生——搬到隔壁之后才发生了变化。
我拿起一瓶陈年的法国柯纳克白兰地,这是我在餐具柜里找到的,然后往咖啡杯里倒了一些。
我此次回美国的目的与这间房子以前的住户——乔治和埃塞尔有关,他俩是斯坦诺普庄园的家庭用人。乔治是个好人,不过十年前就死了。他的妻子埃塞尔不像他那么和善,现在躺在收容所里,很快就要跟她的丈夫团聚了——除非乔治与天堂的守门人圣彼得提前商量过了:“不是说好了让我得到永远的安息和平静吗?她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吗?她喜欢热一些的气候。”不管怎样,我现在是负责处理埃塞尔财产的律师,因此我需要处理这一切,还要参加她的葬礼。
我回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间门房目前是我在美国的合法地址。不过很不幸的是,这栋房子很快就要转到一个名叫埃米尔·纳西姆的伊朗人手里。斯坦诺普庄园的主宅以及庄园里大部分的田地——包括那栋客房楼——现在都归他所有。不过,目前埃塞尔·阿拉德仍然拥有在门房的终生居住权。也就是说,在她去世之前,她可以免费租住在这里。这栋免费居住的房子是苏珊的祖父奥古斯塔斯·斯坦诺普给她的(因为埃塞尔当时曾对他施加了压力)。埃塞尔非常友好地允许我把我的东西存在她这里,并且我每次回美国都让我到她这里来住。埃塞尔心里恨我,不过那就说来话长了。不管怎样,埃塞尔在这栋门房和这个星球上的租住期就要到头了。所以,我从伦敦回来不光是为了向她告别,还要为我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找一个新家,寻找一个合法的新地址,这对一位公民和债权人来说似乎是必须要做的。
这是自去年9月份以来我第一次回纽约,上次我到达伦敦机场时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来到纽约后我在耶鲁俱乐部待了三天,因为偶尔要回纽约出差,我保留了这里的会员身份,看到这个大城市现如今变得如此安静,空空如也,满眼凄凉,我感到非常震惊。
我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一个人也没见。我本来想去看看我的女儿卡罗琳的,但在“9·11”之后,她已经从位于布鲁克林的寓所搬走,到南加利福尼亚的希尔顿黑德和她母亲住一起了。我儿子爱德华则住在洛杉矶。所以,那三天的时间里,我一个人沿着这个城市那些寂静的街道四处晃悠,看到从爆炸核心点的地方仍有黑烟冒出。
我越看心情越糟,于是便乘飞机返回伦敦。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就像是回家料理死去亲人的后事一般。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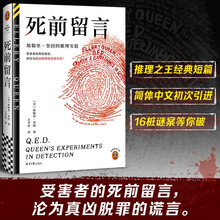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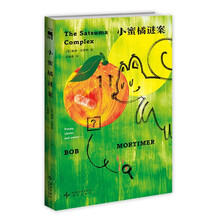



——美国联合通讯社(美联社)
阅读德米勒的小说能让人上瘾,《豪门庄园》就最有说服力,读了它,你就可以了解德米勒的风格。
——《坦帕论坛报》
本书在描写犯罪方面像《教父》一样有趣,但它更幽默,更具自己的风格。德米勒是一位具有原创性的作家,他尽量避免重复。他的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叙述节奏、语言风格和独特的人物性格。他还坚信,故事中那些逼真的谈话和对白更能让读者信服,阅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在偷听别人的谈话。
——《奥兰多前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