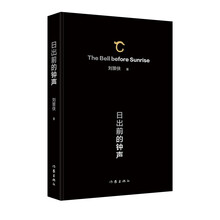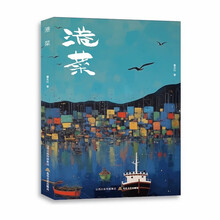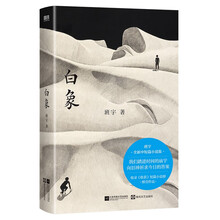引言:凤兮
凤凰是种猛禽,有锐利如刀剑的爪子,吹毛断发,削金如泥;有周身披有的翅羽,水火不侵,百毒不害;有喙,硬逾精铁,无坚不摧,所以父皇叫我“凤皇儿”。在我小的时候,他常常抱我置于膝上,笑吟吟地同我说:“我家凤皇儿以后要当大将军,要给我大燕开疆拓土,威震四方,令天下闻风丧胆。”
我那时年岁尚小,就只会睁大眼睛看着父亲,一板一眼地点头应承:“诺。”
父皇于是笑,对左右说:“此子命犯兵戈。”
我那时候并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不对,我慕容家族是从马上得来的天下,哪个儿郎没有热血,哪个儿郎不向往征战沙场?
但是还没等我长到能骑马的年纪,父皇就过世了。在许多年以后,我只记得铺天盖地的帷幛,将整个邺城都遮住了,放眼看去,阴沉沉的黑,苍茫茫的白,肃然穆然,再没有别的颜色,直到红日一跃而出,金光万丈,鱼鳞浮云在蓝的天幕上依次排开。
大哥不是一个好皇帝,他逼走五叔,是自毁长城;任用宵小,是自掘坟墓。在太平世道里,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但是这样一个乱世,秦失其鹿,群雄并起,天下共逐之,哪容得片刻懈怠?
国破家亡,指日可待。
尽管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却是一个好兄长,他给我最高的尊荣、最大的信任、最多的权柄,中山王、大司马,节制一国兵力,他抚我的顶头说:“冲儿是我家凤凰,当一飞冲天,一鸣惊人……”那年我十二岁。
我的骑射功夫很不错,我训练了自己的卫队,但是当时,在我还没有正经上过战场,调度过兵马的时候,一切就已经发生了。
势如破竹般,国就亡了,城就破了,京都就没了……
我努力想要记起当时的兵荒马乱,那些奔走哀嚎的人,那些沉默的死亡。那些喷薄而出的鲜血,就如同红日般灼烧着我的眼,刺痛着我的心。大哥出逃,并没有带上我,也没有带上他的皇后,但是没等他逃远,,护卫将军就被杀,他也被截了回来。
一拥而入的武士在宫苑里来回奔纵,他们叫嚣着,大笑着。他们杀人,他们放火,他们搜罗和瓜分宫中珍宝;他们肆无忌惮地嘲笑我,嘲笑大哥,嘲笑慕容这个姓氏;他们肆无忌惮地打量宫妃、宫人……还有与我一母同胞的姐姐清河公主,那一日是她被称作清河公主的最后一日。那一日,也是我当中山王的最后一日。我握刀,守在姐姐面前,凶狠地瞪着每一双不怀好意的眼睛,我知道那是徒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是摆出这样一个姿态,至少能让他们意识到,要侵犯我大燕的公主,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面对我慕容家族的屠刀。
那些兵士手里也有刀,但不如我的精美,不如我的锋利,有的甚至刀身开裂,刀刃打卷,但是掩不住的狰狞,就如同他们的面容,煞气凛凛,他们低垂着刀,鲜血从刀尖滴落,落在尘埃里,尘埃覆过,就仿佛黑夜覆过白天,仿佛岁月覆过时光,仿佛烽烟覆过繁华,仿佛鲜血覆过人心。
太久太久,忘了人心是什么样子……一刀劈开,拽出来,滚烫地,鲜活地,还会蹦跳地……最后静默。
我总觉得,我死在了那一日。
就在那一日,大哥对我说:“凤皇儿,你去吧,为了大燕,为了慕容,为了……我。”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深深低垂着头,没有看我,或是不敢,或是不能。那许是哀求,许是无奈,许是漠然。我的目光茫然越过他的头顶,茫然地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想道:他日黄泉之下,他该如何跟父皇解释呢?
后来……我忘了。
从邺城到长安,走了多少时日,我……忘了。
我被安置在长乐宫里,和姐姐一起。这是座非常恢宏非常华丽的宫殿,宫人每次行礼都会说:“长乐未央。”我问姐姐是什么意思,姐姐告诉我说,那是一种祝愿,表示欢乐啊,永远没有尽头。
我沉默,然后我笑了。
我想那一定是个非常可怕的笑容,因为那以后,姐姐就不大与我说话了……不,其实在之前,她也不大与我说话,或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只是尽心尽力地照顾我,但是我却发现,她看我的眼神,分明恨不得亲手掐死我。
她恨我,因她爱我至深;她想要我死,因为这样的日子,的确生不如死。
其实,我也想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死。
苻坚对我很好——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凡我所求,无有不应。他将我的族人迁入关内,但是允许他们聚居;他给我的兄长们体面的官位、爵位,他自己过得很简朴,但是纵容我,极尽骄奢。
珍珠如土金如铁。
于是长安有歌谣:“一雌又一雄,双飞入紫宫。”
这让我想起关于凤凰的传说:凤凰是分雌雄的,雌为凤,雄为凰。汉时司马相如就曾以《凤求凰》赢得文君欢心,文君当垆,司马操琴,但是后来,以一首白头吟而终,我还记得凤求凰里唱,凤兮凤兮归故乡。
我向西眺望,烟尘渺渺,乡关何处,纵山河在,国破家亡。
从冬到春,从秋到夏,我再没有步出过宫室,我的存在,于苻坚是奇货可居,于后宫是一种尴尬,而于我鲜卑慕容,则是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但苻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我,起初也不明白。
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段元妃。
段元妃是我的五婶,容色绝丽。我在御园里碰见她,她原在游园,转眸看见我,于是啐了一口,登车而去。
她也是被苻坚凌辱的人,也知我是不得已,她与我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知道,是不一样的。我是男子,应当金戈铁马,席卷天下,而不是雌伏后宫,取悦于人。我垂头,指甲渐渐嵌入到掌心里去,丝丝渗血。
之后,我离开了长乐宫,迁居阿房城的阿房宫,因为天下臣民的非议,因为丞相王猛的一再上书,痛陈厉害,要诛我以警世人。苻坚同我说:“对不住。”我想他最对我不住的,不是今日,而是破城那天,没有一刀杀了我。
阿房宫里仿佛只有我一个人,从早到晚,孤寂冷清,我不想说话,不能入睡,镜子前面头发和指甲疯长。我想,总有一日,我会疯掉的,在死之前疯掉。
我恍恍惚惚地哭,恍恍惚惚地笑,恍恍惚惚度日。
我记得父皇曾说,凤皇儿以后要做大将军,要开疆拓土,要威震四方;我记得大哥曾跟我说,冲儿是我家凤凰,当一飞冲天,当一鸣惊人……还真是很惊人哪!我凉凉地想,我的过往,我却无言以对
其实他们都错了,凤凰虽然勇猛无俦,但是它是天下最仁慈的鸟儿,它要等天下太平才肯降临人间的啊,这烽烟四起的乱世,如何容得下凤凰?
这烽烟四起的乱世,我怎么就……来了呢?
我是被缚的凤凰,烈火熊熊,烧盲了我的目,烧残了我的爪牙,烧毁了我的翅羽,劫灰重重,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涅槃重生,让天下都听到我的清啸声,痛哭声,吼叫声,让这自我心中迸发的烈火,将这龌龊世间,付诸一炬?
忽然,我听到了一声古怪的鸣叫。
一 遗世孤者
我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悠悠唤醒。
很难说我到底是被饿昏的还是饿醒的,总之醒来以后唯一的感觉就是饿,很饿。我眼睛里荧荧放出光来,绿油油地盯住眼前的活物,像一匹来自荒原的饿狼——啊,我知道这个比方是不合适,太有失我的身份,但它不过就是一比方不是?
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是,我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深情地呼唤着食物的名字。
而眼前这个活物只冷冷地看着我,没有更多表情——他是个穿白衣的人类少年,苍白的一张小脸,风吹过去,衣袖啊衣摆啊衣领啊都被风吹得飘飘的,猛一看,这不是白无常大叔吗?
不对!
白无常哪有这么好看的!
月色如轻纱,整个人如同冷玉雕成,有种微凉的质感,墨鬓似刀裁,浓眉如远山,清目含秋水,秋水太明亮,映出我的贼眉鼠眼是如此的猥琐,这个事实让我不得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长老们的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长老们都说,横看竖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看,我都不像是一只凤凰。
我是一只凤凰,原本这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实,但是后来,它变成一个可信可疑的传说。
这样说吧,起初我是一枚凤凰蛋,就好像每只鸡都曾是鸡蛋;后来我破壳而出变成了一只雏凤,就好比鸡蛋变成小鸡;再后来,就当我快要摆脱菜鸟地位的时候,长老们忽然开始集体质疑我的身份。
笑话!
你能相信吗,凤凰蛋里钻出来的不是凤凰而是山鸡,又或者鸡蛋里钻出来的不是鸡而是鸭。
总之,这是极端荒谬的一件事情,但是长老们就这样质疑了,他们认为我可能是一只毕方,或者玄鸟,或者孔雀什么的,但是这些质疑都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昆仑山的鸟类都是有尊严的。
比如毕方,他们坚决认为我身上缺乏毕方特立独行的优良品质——有道理,你见过有别的动物像毕方一样,长了两只脚,却只有一只翅膀、一个脑袋的吗?所以也没有别的动物敢跟他们比“独行”了。
玄鸟的反对意见也很有见地,他们说:“我们玄鸟有胖成这样的吗?”——起先我是真的不相信我能用“胖”来形容,但是后来有一天我试飞时不小心撞上一截枯木,而那截枯木居然会嗷嗷呼痛的时候,我就信了。
长成这样一副比排骨还排骨、比骷髅更骷髅的尊容,我实在不忍心多说什么。
而孔雀们一律鼻孔朝天地冷哼:“有这么丑的孔雀吗?”
——这话不对,应该说,有会飞的孔雀吗?我还头一次知道有鸟儿只能从高处往低处飞呢,那能叫飞吗?我是丑了点儿没错,起码我会飞,所以我每次看到孔雀,都会拍拍翅膀,拍他们一头一脸的灰,然后得意洋洋地飞远。
总之,昆仑山的各大种族都不肯认领我,我只好委屈自己仍然作为凤凰中的一员,只是有点儿爱掉毛而已。
没有错,我是一只爱掉毛的凤凰。
不记得是从哪年哪月起,我开始大片大片地掉毛,起先我周围的鸟儿——无论是凤凰毕方,还是玄鸟孔雀——都挺兴奋,毕竟,遇上一只掉毛的鸟儿不容易啊。他们整天整天地守在我的身边,捡毛回去充实自己的窝,到后来,那毛掉得也忒狠了,我飞到哪里,哪里就平地刮起龙卷风,我的眼睛一眨,地上就陡然厚上三尺,如胭脂、青鸟之类的小型鸟类,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被活埋了,而走兽们也开始经常性地迷路,一只恶狼迷路栽进兔子窝,那叫惊喜,一只小羊迷路闯进老虎的地盘,那叫悲剧。
显而易见,金山银山也禁不起这样的折腾,所以三年之后,我变成了一只秃毛凤凰。
所谓人有秃顶,凤有秃毛,我有什么法子呢?
真正的凤凰,应该勇于面对秃毛的窘境。
但是长老们不这样认为,他们特别渴望别的种族能把我认领了去,只是都没有成功,经过三年三个月零三天的研究,一个特和蔼的长老被派来游说我,他说:“阿朱啊,只要你能够经得起涅槃的考验,浴火重生,那么我们就承认,你是凤凰。”
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老被我一翅膀拍飞——我傻呀,万一我真不是凤凰,火一烧,哎呀呀,大伙儿就眼巴巴等着吃烤鸡是不是?
我愤愤地想,在长老们计划将我架到火上猛烤的前一天打包逃离了昆仑山。
下山才知道麻烦。
还在昆仑山的时候长老就告诫过我们,人间是一个非常污浊的去处,我们凤凰只有落到梧桐树上才能够安稳地睡上一觉,只有吃竹实、饮醴泉,才不会闹肚子。原本以为人间遍地都是梧桐,到处都可以找到开花的竹子和清澈的醴泉,下山才发现,原来这三样东西,在人间都是很罕见的。
我常常飞了几天几夜,都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常常饿了几月几年,才能够找到一点可以入口的食物和水。
所以没过多久,当我有机会在水边顾影自怜的时候,就发现水里与我深情对望的那家伙,怎么看怎么像一只玄鸟。
但是对我来说,一路再狼狈,也狼狈不过这个晚上——因为我在这个人类少年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类似于掉毛野鸡的动物,我抬起翅膀来擦擦眼睛,觉得以我当前的形容,如果还被称之为凤凰,长老们一定会让我后悔出壳一遭。
郁郁然叹了一口气。
很远的地方传来水滴的声音,竹米的清香,很安静的晚上,月光皎皎照在少年的眼睛里,黑得像玉,亮得像玉,冷得像玉,真是一个玉雕人儿,刀刻斧削的眉目,好看得不像真人,也冷得不像真人。
冷……太冷了。
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伸出翅膀去摸摸他的头顶,想试探有没有热气,但是他闪身躲开了,他用一种奇怪的目光上下打量我,仿佛在问:“你是谁?”
“我……我叫阿朱,你呢?”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理会他的注视,不理会他的疑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想要回答他。
少年愣住,许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我、而我都快要睡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极困惑又极期待的声音:“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废话,知道还问什么,我很用力地朝天翻个白眼表示鄙视。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你可以叫我凤皇。”
啊啊啊啊啊啊……我猛扑上去想要站到他肩上以示亲热,结果力有未逮,一头栽了下去,幸好我眼明爪快,及时抱住了他的大腿——在人间流浪这么久,终于让我找到同类了,我激动得泪流满面,然后再度昏迷过去。
很难说,是饥饿,还是过度的兴奋导致了我的昏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