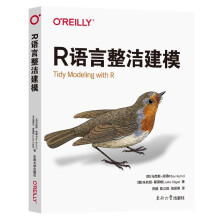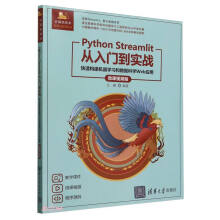我们生活在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无可奈何,也无法逃脱,而对这种处境我们每人都有责任,我们中间最革命的人也不例外。窒息空气的原因之一在于对一切写出来的、列出来的、画出来的东西,总之已成形的东西毕恭毕敬,仿佛表达尚未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仿佛事情尚未处于应该大破然后大立的境地。
应该和杰作的概念决裂,杰作只属于所谓的精英,群众根本不懂。应该提醒自己,在精神中是没有保留区的(而生活中有秘密的卖淫区)。
过去的杰作对过去是适用的,但不适用于我们。我们有权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说已经被人说过的话,甚至不曾被人说过的话。我们的语言是立即的、直接的、符合现今的感知方式,而且人人都能懂。
责备群众缺乏崇高感,这是可笑的,这是将崇高与某种形式表现——而且永远是死去的形式表现——混为一谈。如果说今天的群众看不懂《俄狄浦斯王》的话,我要说那该归罪于《俄狄浦斯王》,而不该归罪于群众。
《俄狄浦斯王》有一个乱伦的主题,它还暗示自然如何揶揄道德,暗示某处有种游荡的力量,我们切要当心,这力量叫做命运或别的名字。
此外还有瘟疫流行病,它是这种力量的有形体现。但是这一切都穿着某种礼服,操着某种语言,而它们与今天狂乱粗鲁的节奏完全是两回事。索福克勒斯嗓门可能很高,但讲话方式已过时了。他讲得很细,但今天的人听不懂,还认为他在答非所问。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