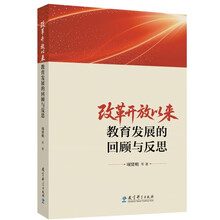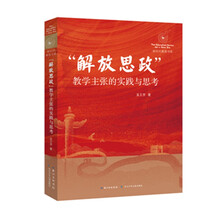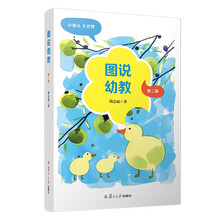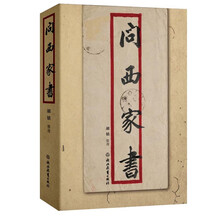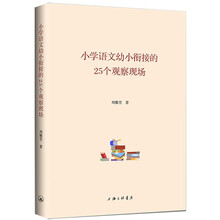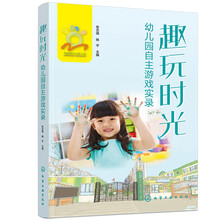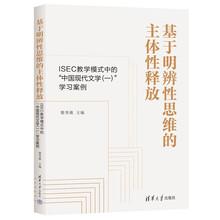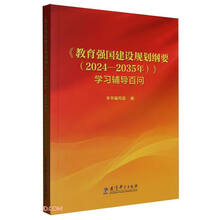孔子官运亨通,由鲁国的中都宰升迁为司空,又擢为大司寇,兼摄相事,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段时间他的收入当不在少数,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就是在此之后,也说明这时他的财力已不同于从前。
再次,来自富裕学生的赞助。对于《论语·述而》中“自行束修以上”这句话,学界争论颇多,其中一个焦点就是“束修”是否是孔子向学生收取的学费。其实,抛开“束修”本身的含义,从“自行”两字来看,必须是学生自愿交纳的财物,因此“束修”就不应该是学费,但若不交“束修”,就不能人学,故既可理解为“拜师礼”,同时也可理解为学生对私学提供的“赞助费”。而从“以上”两字来看,说明这种“赞助费”并不限于十条干肉,孔门弟子中多为达官贵人子弟,起码也是生活略为余裕的庶民。如《左传》载,鲁国大贵族孟僖子将死,命其二子去跟孔子“学礼焉,以定其位”,他所交纳的“赞助费”肯定是“束修以上”。再如子贡出身于“结驷连骑”“家累千金”的商人家庭,本人也是春秋时期的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说他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他给孔子交纳的也绝不会只有“束修”,即便让他“独资”来供养孔子私学,也绰绰有余。
最后,通过培养学生入仕获取一部分报酬。“学也,禄在其中矣。”这大约也是孔子本人的经验之谈。虽然他做官的时间并不长,但他的学生却遍布各诸侯国的朝廷之中,见于《论语》及《史记》的就有:子路、冉求做过季氏宰,卜商做过莒父宰,言偃做过武城宰,宓不齐做过单父宰,子贡做过鲁相、卫相。还有一些学生拒绝入仕,如季氏曾多次派人聘请闵子骞去做“费宰”,闵子骞均不愿前往。孔子私学弟子在各国是颇受欢迎的。这些学生入仕,或由孔子举荐,或由同学推荐,或由诸侯礼聘,在以礼相请的同时,自然不可能没有一点物质上的表示。这虽含推测性质,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