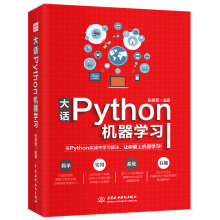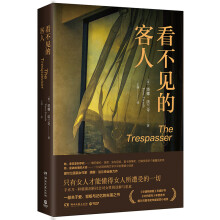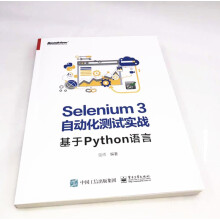不言而喻,福泽谕吉的观念在此得到进一步的弘扬,中日之间的战争使福泽谕吉的思想得到深刻的体现。站在东亚文化的内部来否定中国,进而侵略与侮辱东方民族,且站在现代文明的制高点,通过设定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坐标,日本为自己发动的战争找到现代文明——实质上是西方文明体系下的合法性。就在这样的唯政治性的现代地缘政治之中,中国成为了一个被日本奴役的他者。正如德富苏峰在1894年发表的《大日本扩张论》中所言:“本书……的目的在于论述大日本的扩张,也就是将征清作为论述大日本的扩张这一问题的前提。有征清未必有扩张,有扩张才有征清。”①征服与奴役“中国”这一他者,成为日本确立自我身份的前提与手段。而且,日本的地域条件也决定了它必须以中国为前提或者手段。事实上,日本并不是所谓的被动的、隐蔽的、暧昧的主体,而是一个始终抱着独特的、绝对的、自由意志的思想主体。
为什么德富苏峰会重视“大日本扩张”的问题?就德富而言,明治维新的开国只是日本“形式上的解脱而已,事实上收缩的枷锁依旧控制着每一个人,因此,精神的解脱不可不谓之在于征清之役,此乃精神的开国,而后方有真正的开国也”。在此,日本与中国的战争成为德富唤醒日本民众、实现平民主义、推动精神性的开国的一大契机。换句话说,就是将中国作为一个工具性的他者,只有克服了这样的他者,日本才能获得真正的开国,才能拥有真正的自信与自豪。在德富看来,日本要维持国家的生存,维护乃至扩张自己的国际地位,就必须进行“军备扩张”,这是日本作为“新兴国”的“国民的使命”。②
德富苏峰的“变节”或者“变故”,其根源正如《自传》所叙述的,“辽东还付(著者注: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日本返还辽东)事件,可谓左右了我一生的命运。自闻此事以来,我在精神上就几乎成了另一个人。若是要我来讲述的话,也就是深感自身力量的不足。如果我们自身的力量足够强大,我相信任何所谓的正义公道都不值半文钱”。③在此,德富自人生最初的“宗教的和平信仰”直接转向了一种“力量”的逻辑,并相信所谓的正义公道在面对实力之时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的逻辑,也就注定了其会进一步追随日本军国主义的脚步,不断地走向亚洲扩张的道路,从而蜕变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在这种观念的左右之下,德富成为了一名大力提倡“东洋自治论”的人。而所谓的“东洋自治”,就是日本以“文明”的武器去杀戮“野蛮”的亚洲人。
福泽谕吉确立下来的“文明·野蛮之战”的基调,为那一时代几乎所有的日本知识分子所继承。内村鉴三提到这场战争时说,这是“新而小的日本与旧而大的支那之间的冲突”,是一场“进步”与“退步”的精神的冲突;①植村正久在《日本评论》中提到:“日本的天职就是顺应历史的潮流,举公明之君民同治之政,彰扬自由之大义,率领亚细亚之诸邦国,耕耘文明之田野,挽回东洋之颓势”②,故而这场战争的动机在于“新旧两样的精神冲突”,乃是“大日本帝国将自我意识开化进步之天赋,向全世界予以披露的一大时机也”。③
不过,与德富苏峰转向“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不同,作为基督教徒的内村鉴三尽管一开始站在文明进步的视角认为这是一场“义战”,但是而后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相信打倒支那,而后日本应该崛起的人,不可不称之为最不了解宇内大势之人。东洋的和平来自振兴支那,朝鲜的独立、日本的进步,应该同是支那兴起的(真正的)结果……以支那的废灭来谋求东洋的和平与安全,乃是最为自欺欺人者也”。④也就是说,国家的进步与独立乃是一个超越“自我·他者”的差异,必须加以尊重的普遍真理。而且,这样的真理完全应该超越国家这一范畴。以追求自身的独立来压制他国的独立,以突出自身的力量来强制性地占领他国的领土,所谓的独立或者解放,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伎俩而已。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作为“他者”,冷静地看待中国的“失败”,并由此产生了一种蔑视中国的情绪。甲午战争的结果,延续了中国近代以来对外战争不断失败的历史,也使这样的蔑视感普遍地存在于日本人当中。如果说过去日本对中国的认识还是基于同为亚洲国家这一前提,且中国不过是一个“冥顽固陋之国”而已的话,那么经过了“脱亚”、“人欧”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之后,日本则是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野蛮”框架下的文化他者,同时也由此而出现了以蔑视论为背景,“指导”或者“解放”中国走向独立的一股思潮。这样的思潮成为战争期间的思想主流,且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