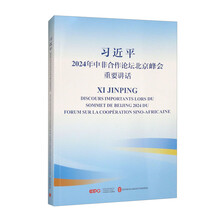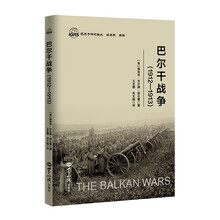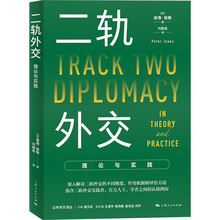后来,《叛逆者》作为有岛著作集由新潮社出版时,又补入了《米勒礼赞》和《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这两篇著名评论。迄今为止,当人们语涉惠特曼和郭沫若的关系时,或许为资料所限,根本无一人重视作为重要媒介者的有岛,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研究领域里的一大缺陷。
不但有岛传神译出的《草叶集》诗行影响了郭沫若,绝不撒谎的有岛那真实的自我心魂暴露,也强烈震动了郭沫若的灵魂。有岛那些诚实的灵魂告白,《草之叶——关于惠特曼的考察》中流淌的寻求主体意志与情感的自我回归意识,以及确立正当的“自我中心”的存在价值,又配上惠特曼那些启人深悟的长诗,珠联璧合,浑然一体,才给郭沫若以全新的印象,使他那躁动的灵魂,深受震撼。他引吭高歌:“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郭沫若:《女神·晨安》)接近惠特曼之后的郭沫若曾激动自述:
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序我的诗》,《沫若文集》,第13卷。)
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都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
我的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太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是“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7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