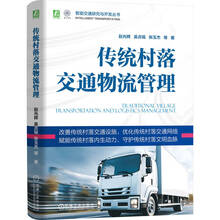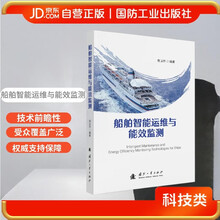导言<br>一交通史与人类文明的总进程<br>早在人类历史的初年,远古先民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往往不得不辗转迁徙,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在开始经营农耕养殖之后,依然“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早期交通的发展,是人类距今最久远的富于开创意义的成就之一。最原始的道路和航线,形成人类文明在这个星球上留下的最初的印迹。中国远古传说中著名的夸父追日《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愚公移山《列子•汤问》:“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等故事,即借助神话方式,使得人类早期开拓交通事业的英雄业绩保持着经久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在漫长的数以万年计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交通的进步总是同人口和需求的增长,同生产力的发展,同文化的演进呈同步的趋势。在探索史前文化的面貌时可以发现,时代愈古远,则不同生活情境下人群相互间的文化差异愈明显,甚至相距不远的人类居住遗址的同时代的出土物也表现出鲜明的各自相异的特点。经过长期的交往与沟通,才逐渐显现越来越突出的文化共同性,于是导致具有共同文化特点的部落、部族、部族联盟乃至民族的形成。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形成与存在的首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前进。相反,在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每一种发明往往“必须重新开始”,历史上甚至多有相当发达的生产力和一度极灿烂的文明由于与其他地区交通阻断以致终于衰落毁灭的事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切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重要的影响。导言秦汉交通史稿人类不断深化对自身历史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生产”对于历史进步的意义。他们同时又突出强调“交往”的作用,认为:“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他们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24页。在论说“生产力”和“交往”对于“全部文明的历史”的意义时,他们甚至曾经取用“交往和生产力”的表述方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56~57页。“交往”置于“生产力”之前。此说“交往”,实与“交通”近义。有交通理论研究者说:“交通这个术语,从最广义的解释说来,是指人类互相间关系的全部而言。”[德]鲍尔格蒂(RVon der Borght):《交通论》(Das Verkehrswesen)。转引自余松筠编著:《交通经济学》,3~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所谓“人类互相间关系的全部”,可以理解为“交往”。中国古代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通其交往”(《尉缭子》卷三《分塞令》)、“通交往”(归有光:《震川集》卷八《上总制书》)的说法。交通发展在历史进程中的突出作用,使得交通史逐渐成为学人瞩目的研究课题。<br><br>二交通史研究的对象<br>交通,古籍中意义或为交和会通。《易•泰》说:“小往大来,吉,亨。”《彖传》:“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管子•度地》:“……桓公曰:‘当何时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所谓“交通”,是体现出生机、活力和新鲜气息的运动形式。秦汉史籍中“交通”往往取交往之意。《史记•黥布列传》:“布已论输丽山,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灌夫“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桀大猾”。《汉书•江充传》:赵太子丹“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礼记•乐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交通”与“四达”并称,言交汇通达,无所不至。而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谓“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则更近于今义。今人所谓“交通”,意义也有狭义和广义的不同。狭义的交通,指有意识地完成的人与物的空间位置的转移。广义的交通则除此之外,又包括通信等信息传递方式的运用。前引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交往”的论述,实际上涉及一般所谓“交通”的更宽广层面的社会文化意义。交通除了人员与物资的直接的转运输送之外,还应包括社会交往的若干其他形式。在这一认识的基点上来讨论秦汉时代交通发展的现象和规律及其对于社会文化面貌的作用,应当是有意义的。我们基本赞同这样的意见:“交通为诸社会现象生成不可避的必然的手段。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与其他一切社会现象之成立,当依赖于交通之支持。因此交通发达,当直接影响于上述各方面。”余松筠编著:《交通经济学》,37页。由此出发设计的研究路径,除对当时交通发展的具体形态进行必要的技术层面的考论,进而研究交通的具体的生产机能,分析交通的直接的经济作用之外,对交通的社会的功用和文化的机能也投注相当多的注意力,对交通发展状况对于社会文化史进程的影响,交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希图有所探索,以增进对历史的全面认识。<br><br>三秦汉交通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中的地位<br>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秦王朝。此后440年间,除秦汉之际和两汉之际出现短暂的分裂局面而外,始终维持着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统治。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新的生产关系得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实现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中国专制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也在秦汉时期表现出来。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秦汉时期主要社会经济部门农业的发展,完成了重要的飞跃。人们常常注意到,汉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甚至直到近世仍没有根本的变化。交通事业在秦汉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专制主义政权始终将发展交通作为主要行政内容之一。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备的交通运输系统,成为秦汉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强大支柱,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统一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秦汉交通的主要形式为以后两千年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考察秦汉时期交通发展的状况,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沟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主要经济区的交通网已经基本形成;舟车等运输工具的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路桥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出现了新的形式,运输动力也得到空前规模的开发;交通运输的组织管理方式也逐步走向完善;连通域外的主要交通线已经初步开通;在当时堪称世界先进的交通条件下,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的文化——汉文化已经初步形成。呈示这样一部以秦汉时期的交通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笔者除了希望以新的视角更全面地、更真切地描绘秦汉社会文化风貌而外,还试图仿效生物学研究中“切片”以供显微和超显微观察的技术步骤,通过对秦汉这一历史阶段交通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增进对整个中国古代交通史之特点与规律的认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