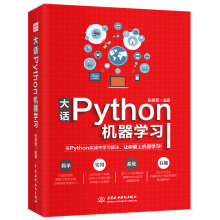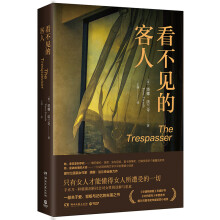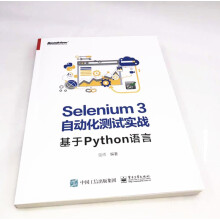在那些维系于产权习惯的依附型社会中,商人的财产得不到正式规则的有效保护,或者沦为被侵犯和掠夺的对象,或者庇荫于潜规则层面的产权习惯之下、护佑于以个体商人和家族为单位进行的钱权交易和官商勾结之中。商人的财产时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在长期中阻碍了规模性投资和经济增长。后进国家的产权结构大多系属此类。在那些发达的收买型社会中,由于正式的产权规则的保护和偏袒,商人的财产规模和势力得以膨胀。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些正式规则是将统治阶层与商人阶层的共同利益合法化的产权分配方式。在正式的产权规则下,两个主导阶层之间,由相互利用的关系逐渐融合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暧昧关系。双方主要不是相互对立的、讨价还价的博弈者,而是具有一致的利益、彼此界限模糊的合作者,是占据国家统治地位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职能分配。
统治阶层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微妙而且复杂;非中性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究竟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其间的界限也异常模糊。它们之间也许本来就互为因果。在我们所研究的大国“起飞”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则是二者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统治者天然地具有追求自身强大的倾向,而新兴商人阶层也同样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他们的既得财产、实现他们无止境追求财富的野心。意味深长的是,在追求民族国家强大这一目标上,他们的利益融合交汇了。一方面,国家和其统治者为商人阶层提供产权保护和扩张支持;另一方面,统治者和他(们)所掌控的国家权力的膨胀也同样离不开新兴商人阶层在财税和政治上的“助阵”,更何况君主本人也直接从对外扩张中获益匪浅。更进一步说,国家利益说到底还有由其背后的个人利益所组成。当商人阶层的势力逐渐渗入国家政权内部后,二者利益之间的界限自然变得更加难以辨认。鸡生蛋也好,蛋生鸡也罢,问题的关键在于,商人阶层与统治集团之间形成的共同需求或达成的某种默契使得奥尔森定义的“共容利益”得以不断扩大①,进而诺斯国家理论中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也变得协调起来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