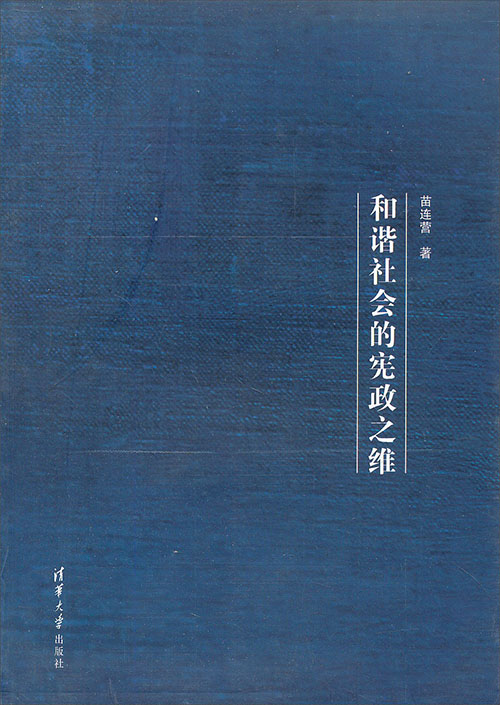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自由法治时期,出于对个人利益过于绝对的坚持和偏好以及对旧时代专制政权的心有余悸,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权力及行使权力的人持怀疑和猜忌态度基础上的对立关系。各项宪政制度的设计都刻意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以尽可能扩大公民能够自己主宰自己事务的自由空间。宪政的主要精神就在于划定国家权力的边界并为其设定一套理性的运行规则和机制,一切国家权力的运行都必须置于宪法预设的控制之下。对权力予以有效地防范和制约是保证个人权利不受政府权力肆意侵犯的制度性前提,“人人生而平等”、“政府的正当权力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等这些脍炙人口的宪法格言及其制度设计精炼地表达了人们对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本质性认识与重新定位。这种体制对于前宪政时期那种个人是权力奴役的对象并依附于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矫枉过正的意义,是对国家利益吞噬个人利益的彻底否定。同时,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使得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衡量成为必要和可能。
然而,对个人利益的过度张扬、对国家权力的过度限制,使国家在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公共利益的漠视甚至否定,阻碍了公益与私益衡量机制的形成。同时,早期宪法所许下的平等、自由和人权等美好的诺言,在许多情况下也成为流于形式的画饼;人们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实际上的悬珠无情地冲击着宪法中的政治理想。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发了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的一系列变革,“有限政府”不再是宪政的全部,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势所难免,“福利国”、“行政国”悄然成为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自然法学派的人权理论在实证主义尤其是社会连带主义的不断夹击和挑战下,难复昔日的尊荣。个人权利的绝对性受到修正,所有权及契约自由等受到来自公法上公共利益的限制。国家与被治者之间不应该是对抗和冲突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社会连带关系,作为“政治动物”之个人的利益必然要受到社会公共利益的约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