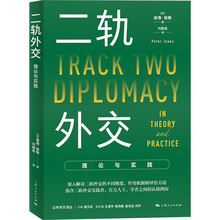代序:重视对公共外交实践的研究——借鉴外国在华开展公共外交的做法
庞中英
学习、研究和实践外交的人都知道,外交一般分为两大部分,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对外交研究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外交理论,而是外交实践,因为外交实践是产生外交理论和更新外交理论的主要源泉。
为了更深入和正确地理解公共外交,即发展公共外交理论,我们需要从研究公共外交实践开始。“公共外交”只是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在实践的意义上引入中国外交。这当然不等于中国的外交刚开始接触和进行公共外交。事实上,一些中国的外交研究学者在此之前就引进了这个概念。在2011年组建中国外交部“公共外交办公室”之前,中国外交部早已形成了一些现当代公共外交的基本体制或者其雏形,如新闻发言人、建立与维持外交部网页、接待公众制度,以及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外交档案等举措。如果将中国已经存在了大半个世纪多的“人民外交”、“民间外交”等考虑进去,中国公共外交的历史也一样很长。
引入公共外交的好处是:可以把类似的与关心、关注外交事务的公众进行沟通的行为(包括解释、说明外交政策、负责地向公众交代、报告外交成绩和问题)充分地制度化、规范化,便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在外交制度上比较健全、发达的国家,普遍具有公共外交方面的体制安排。
一、关于什么是公众外交
外交是政治。传统上,外交是政府、政权(不管是否为主权)之间的政治事务。外交演变到现代和当代,更加复杂,就不仅仅是政府、政权之间的事情。政府、政权沟通、谈判和交涉的对象日益包括许多非政府或者非政权的个人与其组织(所谓“非政府组织”)等社会的公共的力量。这是外交历史发生的最大转变。
现代和当代政治是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的过程和结果之一是民众以及其组成的“公民社会”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进入外交进程。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早已发生。而信息时代更为“公众”介入外交进程提供了物质的基础便利。这里的“公众”至少应区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内公众,一是外国公众,任何外交政策,其制定(决策)和实施,都处在两类“公众”之间,即公众是外交政策中的一大因素。
中国出现了“公众外交”热潮。但是,不少情况下,在这一“公共外交热”中,我们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却存在着不少问题。有时候词不达意,对“公众外交”认识缺少深度和历史感,甚至有令人吃惊的误解。例如,从美国引进的“public diplomacy”理解为“公共外交”就未必确切。在中文语境中的“public”一词,不应该不加以区别,就一律套为“公共”(“公共”一词的使用目前泛滥成灾)。“公共”太抽象而难以正确把握。“public diplomacy”应该与一目了然的“人民”、“公众”、“公开”、“民众”等联系在一起。另外,这里的“公众”,既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而“公共外交”一词显然忽视了这一外交的最重要方面,个体的、非政府的“公众”与外交的关系。早在1963年,美国信息局(USIA)发言人Edward Murrow就把“公众外交”看作是政府与“非政府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互动。所以,笔者并不赞同把“public diplomacy”翻译为“公共外交”。然而,目前,“公共外交”的说法似乎约定俗成,我们也只好从俗。
直到今天,打开任何一本典型的英美“外交政策研究”导论,都会发现,“宣传”仍然是最重要的贯彻落实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与许多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对别国的“宣传”嗤之以鼻的美国媒体,却避谈美国庞大的外交宣传。但是,不幸的是,在世界外交体系中,由于民智开化,“宣传”手段的效用愈来愈下降,所以,才有“公共外交”取而代之。美国也许是最先意识到“公共外交”远比“宣传”的效果要好。然而,即使在西方,许多批评者还是尖锐地指出,“公共外交”仍然不过是名声不好的“宣传”的最新包装。确实,“公共外交”与“宣传”在内容和形式上,难解难分。如果不能把握“公共外交”的实质,“公共外交”确实易被认为是换汤不换药的“宣传”。
把“公众”变成外交的对象和手段,并非当代外交现象,但把“公众”的重要性和战略性提到外交策略的优先,却是最近几十年世界外交的重要发展。正是由于“公共外交”越来越普遍,外交才越来越被区分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公众外交”自然属于“非传统外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