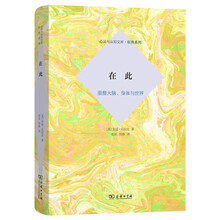第二个迹象表明,罗尔斯最大平等的自由原则及其优先性规则(“自由只能出于自由的缘故而受到限制”)现在只限于意指诸基本自由权项;这是他小心翼翼而又一再重申的一个解释,即尽管对他来说拥有财产的权利是一种“自由权项”,但是对生产资料的私有资本主义与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之间的选择却因正义诸原则而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生产资料是否应当私有的问题,乃是一个社会必须根据其对自己的实际情势以及社会和经济效率之需求的认识做出的抉择。不过,根据这些理由而做出的将私有制局限于消费品的决定,与将私有制适用于所有形式的财产的决定相比,当然会导致一种较为狭窄的自由形式。如果罗尔斯在撰写《正义论》的时候仍在推进那项所有的人“对最广泛的自由必须拥有一种平等权利”的一般性原则,那么他关于这一限制在正义上讲是允许的论断就会使他的理论出现明显的前后不一致,因为根据优先性规则,除非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任何形式的自由都不能因为经济利益的缘故而被缩小或限制。
上述讨论强有力地支持了这样一种解释,即罗尔斯最大平等的自由原则,正如在《正义论》一书中所阐发的那样,所关注的只是那些列举出来的基本自由权项,尽管他只是用宽泛的术语对这些基本自由权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我承认,这个解释还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而这些棘手问题表明,罗尔斯并没有完全否弃其早期的一般自由学说,即使如我在上文所解释的那样,罗尔斯早期的自由学说与其后来认为可以对财产权进行某种限制的观点并不真的相一致。因为似乎很明显,有一些重要的自由形式——性自由和饮酒或吸毒的自由——显然不属于罗尔斯简略描述的那些基本自由权项中的任何一项;[32]然而,如果正义诸原则对限制这些重要的自由形式保持沉默的话,那也会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的。自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以降,这些自由权项便一直是人们在讨论刑法及其他社会强制形式之适当范围时的争论焦点;而且事实上,《正义论》一书中也只有一段文字清晰地表明,罗尔斯认为他的正义诸原则对限制这些自由权项是否正义的问题并未保持沉默。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某些形式的性关系仅仅因为是丢人的或者是令人害羞的、进而不符合某种“至善主义者”的理想(some“perfectionist”ideal)而应当被禁止;在反驳这种观点的时候,罗尔斯指出:第一,我们不应当依凭这种至善主义者的判准,而应当依凭正义诸原则;第二,根据正义诸原则,人们无法为限制这种自由提出合理的理由。
在这小段文字中,就有许多地方我不明白。罗尔斯在这段文字中指出,在限制这类行为之前,正义要求我们证明,这些行为要么侵扰了其他人的基本自由权项,要么“违背了某种自然义务或者某种责任”。这似乎是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对他在有关基本自由权项的文字中经常强调的那种严格标准(即自由只能出于自由的缘故而受到限制)的一种背离。如此说来,难道还存在一套适用于非基本自由权项的次级原则吗?这个解决方案也有它自身的棘手问题。罗尔斯在这里提到的那些自然义务以及各种责任(诸如信守诺言的责任)赖以产生的那项原则,在他看来,乃是处于原初状态的当事人在选择了作为制度(我认为其中包括了法律)标准的正义诸原则之后,又为个人选择的行为标准。如果为了制止对任何这样一种自然义务或责任的侵害而可以对自由进行限制,那么这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缩小自由的范围,因为这些自然义务包括了在可以甚小代价帮助他人的时候帮助他人的义务,以及尊重他人并以礼相待的义务,同时还包括支持正义制度的义务、不伤害无辜者的义务和不造成不必要痛苦的义务。进一步讲,既然处于原初状态的当事人被认为是先为制度选择作为标准的正义诸原则,然后才为个人选择各项自然义务,那么我们不清楚的是,前者是如何能够把后者包含在内的,因为当罗尔斯讲正义诸原则要求我们在限制行为之前证明它或者违反了基本自由权项或者违反了自然义务或责任时,他的意思是前者包含了后者。
我希望自己没有过分强调罗尔斯仅仅是顺便提及的似乎并不属于其基本自由权项范畴的那些自由权项,尽管那些自由权项在某些著名的自由讨论中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然而,从《正义论》一书中,我却无法知道罗尔斯会如何解决我在上文所提到的那些棘手问题,而且我在下文中还会提出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如果行使这些明显属于“基本”自由权项的自由会违反自然义务或责任,那么这些基本自由权项是否也要受到限制。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