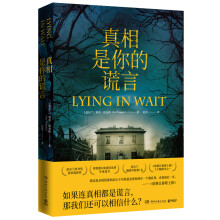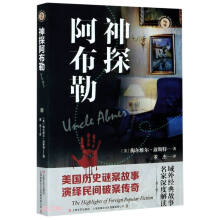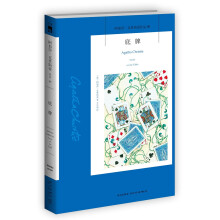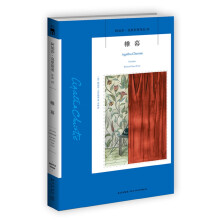使高邮亦日我不配读经,则亦终不能解矣。何也?文史之学,本须读过方解,非不读即能遽解也。初,念孙十余岁时,其父聘东原戴氏为师,授以经籍。当时东原教此未冠小生,当然卑无高论,是以东原在日,高邮尚无所知名。及后自加研究,方能发明如此。昔人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士苟有志,岂可以通儒之业,独让王氏哉?王国维金石之学、目录之学,粗知梗概,其于经学,本非所长,仅能略具常识而已。其人本无意治经,其言岂可奉为准则!正使国维已言不配,若非自甘暴弃,则亦趣向有殊耳。奉以为宗,何其陋也?要之,说经如垦田然,三年然后成熟。未及三年,一年有一年之获,二年有二年之获。已垦二年,再加工力,自然有全部之获。如未及三年而废,则前之所垦,复归芜弃矣。今袭前人之功,经文可解者已十之七,再加群力之探讨,可解之处,何难由七而至八,由八而至九至十哉?高邮创立其法,而有七成可解。今人沿用其法,更加精审,益以工力,经文必有尽解之一日。设全国有一万人说经,集百人之力,共明一条,则可解者已不少矣。假以时日,如垦田之垦熟过半,再加努力,不难有全部之收成。如已垦二年,所收不过一石,即日我不配垦田,岂非怠惰已甚乎?《记》曰:“善学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人之精神时日,自有限制,以高邮父子之老寿(念孙九十、引之七十余),其所著书,尚不能解释全经,则精神限之也。然其研究之法具在。喻如开矿,高邮父子因资本不足,中途停顿,后人以资本继之,自可完全采获。如胡适所举杨树达,已有见端。余虽不及前人,自计所得,亦已不少。况全国学人之众哉?若夫运用之妙,本不待全部了解而后可,得其绪余,,往往足以润身经国。如垦田然,非待三年全部收成之后,始堪炊食,得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时,亦尽可为炊而果腹也。庄子曰:“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胡适宁不知此!以上为正告有志研经之士而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