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人和动物的个体后,我就来比较社会的人和成群的动物,同时寻找我们在一些动物身上,甚至是在最低等最众多的动物身上发现它们拥有技巧的原因。关于某些飞虫的许多事情我们还没谈到呢!我们的观察家异口同声地赞美蜜蜂的智慧和天才。他们提到,这些蜜蜂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一种只属于它们的自治艺术。只有善于观察才能意识到这点。一个蜂群就是一个共和国,每个个体只为集体工作,一切都以一种令人赞叹的预见、公正和严谨的方式来进行安排、分配和分工。雅典古城邦共和国也不比这更有条理、更文明。我们越是观察这个飞虫的群体,发现的奇妙事情就越多:持久不变的管理基础,对于岗位上的每一个体的深深尊敬,特别细致的服务,最最关注的快乐,对集体坚定不移的热爱,难以想象的工作热情,对事业无法比拟的兢兢业业、忘我无私与亲密和谐相结合,用于最典雅建筑的最精确的几何学,诸如此类。我只要浏览一下记载这个共和国的编年史,那么从这些昆虫经历上得到的、博得历史学家赞叹的特点将不胜枚举。
除了我们对观察对象的热情之外,我们总是越观察越要赞美,‘而越少理性思辨。事实上,没有什么比对飞虫的赞叹,比我们给予它们的精神关注,比我们认为它有对公共财富的热情,比我们承认它有最伟大几何学的奇特本领更没有道理的了。蜜蜂只是靠本能迅速地解决了“在最小的空间,以最完美的布局,完成了最坚固的建筑”这一命题的!怎么看我们赞美词中的偏颇之处呢?因为在博物学家的脑海里,一只蜜蜂不应该占据比它在自然界中应占位置更大的地方。在理性的眼光中,这个奇妙的王国永远只是一群除了为我们提供蜡和蜜之外没有其他关系的昆虫而已。
我这里指责的不是好奇心,而是推理和惊叹。我们可以留心观察它们的活动,仔细考察它们的工作过程,准确地描绘它们的生育、繁殖和变化等,所有这些客观事物都可以占据一个博物学家的闲暇时光;但是,我不能接受那种对昆虫伦理学和神学的布道。这是观察家们假设的奇迹,然后他们又当事实描绘出来,说应该加以考察。那种昆虫的智慧、预见甚至对未来的认识被人们赞不绝口,而我就是要还其恰如其分的价值。
这些观察家承认,孤单的飞虫与集体生活的飞虫根本无法相比。前者形成的小群体比大量飞虫形成的群体数量上少得多。蜜蜂可能是所有飞虫中形成群体数目最多的,也同样是最有才能的。这难道不足以证明,精神或才能的表象只是纯机械的结果,只是与数量相对应的运动结合,只取决于几千个个体结合而变得复杂的关系吗?人们难道不知道,所有的关系,哪怕是混乱的,只要固定不变,在我们不知道原因的时候,都显得很和谐。从等级表象的假设到智慧的假设只有一步,而人们为何只喜欢赞叹而不是作进一步深入调查呢?
因此,人们最好将飞虫一只一只分开观察。它们的才能比狗、猴子和大多数动物都要少。我们还会发现,它们并不那么温顺、勤奋、有感情。总而言之,比我们人类的优点少多了。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智慧的表象只是来自于汇集在一起的数量。但是,即使这种汇集也不以任何智慧为前提,因为这完全不是精神意识的聚集,也不是一致意愿的聚集。因此,这个群体只是由大自然安排的有形集中,而与前面所有的观点、认识和推理无关。母蜂同时同地繁殖出一万个个体,这一万个比我假设的可能还要笨一千倍的个体,如要继续生存,就会被迫以某种形式相互调节。因为它们是以相同的力量相互活动,它们开始自相残杀。由于伤亡惨重,它们很快又尽量避免相互伤害,转而相互帮助。于是它们有了和睦相处的气氛,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观察家们却很快赋予它们本身根本没有的观点和思想,让每个活动有理由,每个运动有动机,因而才出现了称之谓奇迹或无数有理性的怪物。这一万个个体,一同出生,一同生活,几乎一同变化,不可能不一同做同一件事情。但它们没有感情和共同习惯,不可能彼此协调、照顾或远离之后又再回来,等等。归结为共和国这一个词的什么建筑学、几何学、秩序、预见、对集体的热情等,都是观察者主观赞赏所引申出来的无稽之谈。
大自然本身不就是够让人叹为观止的吗?更不要说再加上本不存在的又被我们炒作出来的、令我们自己吃惊的奇迹了。造物主因为其作品而相当伟大了,难道我们的愚蠢还能使造物主更伟大吗?如果是,那就是贬低了造物主。究竟是谁从上帝那儿看到最伟大的观念?是那个看着上帝创造宇宙、安排生命、按照永恒不变的法则建立大自然的人呢?还是那个寻找上帝、认为上帝能认真地统领一个拥挤不堪到连金龟子的翅膀都必须折叠起来的昆虫王国的人?
在某些动物中,有一类似乎取决于其成员选择的集体,这种集体比只由生理必需原则组成的蜜蜂社会更接近于有智慧和目标。大象、海狸、猴子和其他几种动物,它们内部之间相互寻找,聚集在一起,成群出没,互相救援、防卫和提醒,步调一致。如果我们不是经常地打扰这些群体,就可以像观察昆虫社会一样容易地观察他们。无疑,我们会看到很多其他奇迹。但这仍然也是生活上的关系和配合。如果我们把同一种类的大量动物聚集在同一地点,由此必然会出现一定的安排、秩序和某些共同习惯。我们将在黄鹿和兔子等的动物史中谈到这些。因为所有共同习惯远不是智慧因素所决定,相反只是以盲目模仿为前提的。
……
P179-183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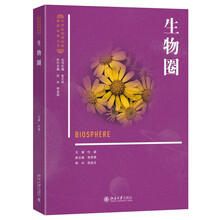


——英国生物学家 达尔文
古代人没有看见过的东西,现代最先进的思想家刚刚看见的东西,布丰将它们通俗地普及了。因此,布丰在自己身上集中了思想的天才和文笔的天才。
——法国科学家 弗卢朗斯
只有布丰给自然情感赋予了全部深刻的含义,将它变成了一种哲学情感。
——《法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