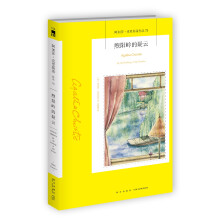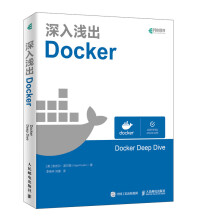而要解释中国与西方社会形成了这种明显不同的格局形成的原因,同为人类,何以不同?制度使然也!中西方社会的文化制度之间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其原因需要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来分析,需要从为什么中国人形成了几乎唯我中心的心态开始。
我们先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柴梱现象”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西方的个体(准确地说是男子),只是团体中的一个组件,具有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的特点,就像蜂群社会中的有蜂王、工蜂和雄蜂;工蜂和雄蜂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与职责;蜂王的任务是产卵,分泌的蜂王物质激素可以抑制工蜂的卵巢发育,并且影响蜂巢内的工蜂的行为。雄蜂的任务是和处女蜂王交配后繁殖后代,雄蜂不参加酿造和采集生产,个体比工蜂大些。工蜂的任务主要是采集食物、哺育幼虫、泌蜡造脾、泌浆清巢、保巢攻敌等工作。蜂巢内的各种工作基本上是工蜂们干的;这种分工明确,责任不同的群体和谐共处。西欧的家庭中,继承制度是单子继承,财产只有一个男子有权承继,其他的男子需要离家出走,这样,同为兄弟,地位完全不同,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可逾越。这种格局促成了兄弟的不同质化现象。
而中国的个体,则是依据自身的需要,不可能成为群体的组件。中国的家庭兄弟之间,存在着同质现象。即财产的均分与承祭祀的不可替代。关于家产继承与中国社会的小农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很多人给予了关注,其中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较早地做了论述,指出其负面的影响。汪兵认为:中华文明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不仅仅意味着一家一户生存的自给自足,还意味着整个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是个有限的“常数”。就像一个家庭收支平衡之后节余所剩无几一样,自给自足国家的税赋劳役在“收支平衡”之后的“结余”同样有限。正是这一捉襟见肘的“常数”,不仅限制了社会的发展——聚敛财富、开疆扩土、商品经济、奢侈享乐、发明创造等所有属于发展范畴的社会行为,统统受到遏制,从而使中华文明成为一种发展缓慢的生存态文明;而且决定了“载舟之水,亦可覆舟”的底线——贫富差距一旦突破这一底线,便很容易将承受力十分薄弱的小农逼上梁山。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