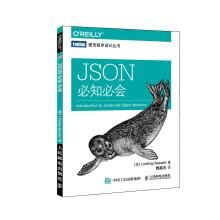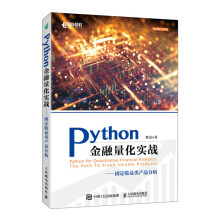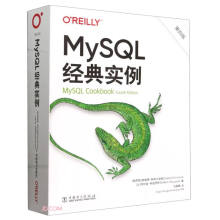亲属称谓自古及今都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众多的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都曾从不同角度对亲属称谓作过专门的论述。由于血缘关系与婚姻制度是产生亲属称谓的基础,所以以此为切人点去探索亲属称谓由来变迁的规律,便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焦点。马良民先生在《由先秦礼俗和亲属称谓看母系向父系氏族的转变》(《文史哲》1987年第5期)一文中从分析“舅”、“姑”、“出”、“姬”四种亲属称谓的内涵人手,得出了这些称谓是父系小家庭已经普遍存在的产物的结论。赵文公先生在《唐代亲属称谓“哥”词义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一文中,通过对唐代“称父为哥”这一现象的探讨,揭示出亲属称谓“哥”所反映的唐代婚姻制度的内容。作者认为导致“称父为哥”这一亲属称谓的流行,体现了唐代皇室、士族中存在着不计行辈的婚姻形态,具有群婚的遗痕。阎爱民先生在其博士论文《汉晋家族问题研究》第三章《亲属称谓制度》一文中,通过对汉晋时期亲属个体称谓的变化进行探讨,揭示出汉、晋时期在婚姻形态、亲属结构及家与族关系等方面发生的巨变社会称谓能够敏感地反映时代、社会的变迁与革新,具有极大的变动性。
由于等级观念的存在,社会关系中官本位的观念十分突出,因而多数学者以探研职官制度的沿革变迁为立足点,对社会称谓的研究作出了一定贡献从帝王称谓的角度而言,郭鹏飞先生在《(尔雅·释诂)“林蒸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探析》(《汉学研究》第18卷第2期)一文中,通过深入分析先秦典籍中的有关史料,对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辨异的工作,详尽地探究出各字词所含的“君”义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所指的相应层面。赵伯雄先生在《两汉“县官”释义》(《历史教学》1980年第10期)一文中,通过对“县”原始涵义的阐发,指出了在汉代“县官”具有代表中央政府与代表天子的双重涵义,并由此揭示出汉人崇古的心态观念。秦进才先生在《“万岁”源流考》(《河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对“万岁”这一称谓的源流变迁情况作了细致入微的阐述,提出“万岁”的演变是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缩影的观点。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