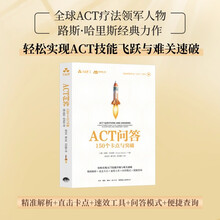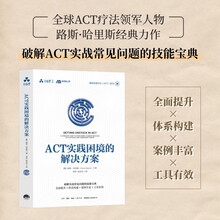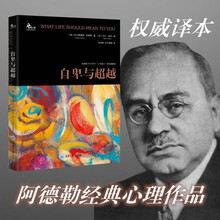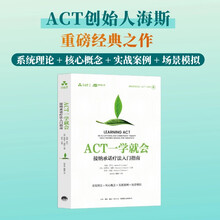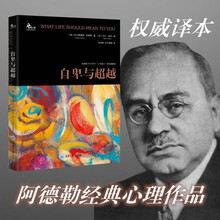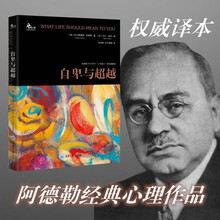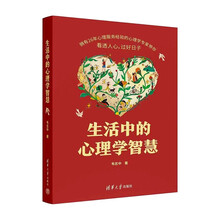少校英格莱姆怪谭
没有人可以在不说谎的情况下赚到100万。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2001年9月10日,少校查尔斯·英格莱姆(Charles Ingram)面临这个考题:数字1后面接100个0是多少?
这是在《谁想当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这个英国(及全世界)最红的益智游戏节目中,闯关的最后一道题。在3次“求助热线”的协助下,英格莱姆正确地回答了前面11问题。此刻,他距离成为该节目史上第三个赢得百万英镑的赢家只差最后一步了。
现场观众经历了他们那两个夜晚的最佳时刻,也为英格莱姆少校不断晋级的表现所着迷。他的特质和之前两位百万奖得主有明显的不同。在2000年,茱蒂丝·卡佩尔(Judith Keppel)成为首位赢家,她拥有英国中产阶级精英的优雅和自信:就算不确定自己的答案,她也不会怀疑自己。在英格莱姆出现的5个月前,大卫·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刚刚赢得了百万奖金,他的自信属于另外一种类型:这位男子深知益智游戏的各种规则和知识,他就像书本沾染尘埃一样收集事实和论据。
相反,英格莱姆充斥着自我怀疑。每个问题都要思索再三,在4个选项中反复抉择,常常自我否定,前一秒钟才被他完全否定的答案,又面临被肯定。至于承受压力的参赛者在面对关键问题时该有的驾驭疑虑的能力,他也完全不曾展现。但不知怎么回事,他就这样踉踉跄跄地给出了11个正确答案。现在他摸索着通往最后答案的道路,答对了会让他赢得100万英镑,答错了则会让他损失50万英镑。
面对4个选项,在已经没有求助热线可以使用的情况下,英格莱姆承认他对答案毫无把握。“你从第二题开始就不曾有把握过。”节目主持人克里斯·塔兰特(Chris Tarrant)调侃道。“我想答案是 nanomole(微毫莫耳),”英格莱姆迟疑道,边用双手捂住了脸,“但也可能是gigabit(千兆)。”塔兰特极力地暗示英格莱姆应该带着目前的50万英镑的奖金离开。有那么一瞬间,英格莱姆好像同意了他的建议。“我不认为自己能够猜对这题,”但是他仍旧坚持,“我认为应该不是megatron(塔型电子管),而且我也不认为我曾经听过 googol 这个词。(googol 这个词是指1后面有100个0的数字,是天文数字、无限大数字的代表。现今知名的搜寻引擎 google 就是经由这个词而来)”英格莱姆在宣布答案前,又念叨了最后这个答案3次。“通过排除法,我确定答案是 googol,但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摄影机对准在观众席中的英格莱姆太太黛安娜的脸,她看起来令人讨厌。“你刚刚获得了50万英镑——你真的要挑战一个你听都没听过的答案吗?”塔兰特充满疑虑地问道。经过了几秒钟的踌躇,英格莱姆用一种下定决心式的口气宣称:“我就选它了。”观众席中传出了惊呼声,这下子,英格莱姆又退缩了:“我得再想想。”但是他还是做到了,他坚持选googol作为最后的答案。在经过中场休息这难熬的耽搁后,塔兰特拿出了50万英镑的支票:“这支票已经不属于你了!”他一边说,一边撕毁了支票。停顿了一下,他又说道:“因为你刚刚赢得了100万英镑!”观众席中爆发出惊喜和解脱般的欢呼。
上面这段录影内容还没来得及播出的一个星期后,当“9·11”事件撼动全球时,英格莱姆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家中接到节目制作公司经理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电话。史密斯通知英格莱姆,塔兰特递给他的那张百万支票已经被注销了,上面的兑现日期正是接到电话后的第二天——9月18日,而本来将于同一天播出的录影内容也被取消了。史密斯只是模模糊糊地提到了“不当行为”,并没有提到英格莱姆和这些行为的关联,英格莱姆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些惊讶,但似乎并不太气恼。5天后的早上7点钟,警察逮捕了他和他的妻子。同时,80英里外的卡迪夫(Cardiff)有第三个人被逮捕:泰克文·维特克(Tecwen Whittock)——在英格莱姆比赛时,他坐在下一批参赛者中的第一排。
一年半以后,在2003年4月7日,伦敦萨瑟克刑事法院判决英格莱姆、黛安娜和维特克以欺诈手法赢得百万奖金;随后,英格莱姆被军队解雇;18个月以后,他宣布破产。
企图窃取百万英镑是正常的,但企图在千万观众面前做这件事,就实在太让人意外了。但吓坏大众的不只是这3个人的大胆行径,而是这起事件的荒谬性。阅读整个审判的过程就好像英式戏剧的剧本一样,充斥着喜剧、狡诈和可笑的自我欺骗。通俗版的内容类似这样:毕业于一所小公立学校、毫不出色的少校被他那充满雄心的妻子说服,为了一夜致富而参与该国最多人观看的节目,利用摄影棚中一位帮凶的咳嗽声——他是益智节目的高手——来引导他选出正确的答案。在克服了万难后,这3个人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直到那天早上,电话响起为止。
这3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清白的,随后虽然有人提供大笔金钱要他们“说实话”,他们也尽力表示自己的无辜。在审判结束后,电视台播放了原本被取消的节目和后续发展的纪录片,有超过1700万观众收看了这个节目——观众人数甚至超过益智节目本身的观众。纪录片剪辑了英格莱姆每一个回合的片段,特别强调少校每次选出正确的答案时,似乎就有人咳嗽。对一般大众而言,这部纪录片提供了一个满足好奇心的平台,让我们看到一个男人是如何在自己精心策划的骗局中被逮到的。英格莱姆对咳嗽的反应非常明显,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我不认为我曾经听过 googol 这个词,”咳嗽声响起。“我确定答案是 googol。”
然而在检察官心中,这个案件有一个奇怪的漏洞: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英格莱姆少校和维特克曾经碰面、交谈或通信。维特克曾经和黛安娜短暂通了次电话,但在益智节目观众的世界中,这根本不足为奇。黛安娜自己也参加过这个节目(曾赢得32 000英镑的奖金),并且曾和别人合著一本关于节目的书籍。另外,想要参赛的人向曾经参赛的前辈们讨教经验也是常事。而警察也没有找到节目结束后3个人联络或见面的证据(你大概能够想象,在英格莱姆赢得比赛后、被警方调查前,这3个人曾经讨论过如何分赃)。在伦敦警察厅的高级警探调查了18个月后,发现刑事法院的判决完全依靠英格莱姆的录影带和塞拉多制片公司员工的怀疑。
经过更仔细调查后会发现,这样的怀疑其实非常脆弱。例如,制作单位告诉法庭,在少校早早就用完了他的3次求助机会时,他们就起了警觉之心。但回顾过去赢得大笔奖金的参赛者,这一点并不特别;又有人指出,维特克有嫌疑是因为他上前询问了小组成员一个问题,但至少有一位先前的参赛者说,这样做没什么不正常;而制作助理则认为,少校说他赢得百万英镑后还会继续工作,这件事让人觉得很奇怪。但之前的赢家爱德华兹在20个星期前就做了同样的事——赢得奖金后继续担任教师。这些证词正是心理学家所称的“事后偏见”(hindsight bias)——我们倾向于想起那些符合我们已经知道的或认为自己知道的思维和感觉。
然而,录影带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节目中共有192次咳嗽,检察官认为其中19次最大声的咳嗽,就是源自英格莱姆的帮凶,但检方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证实这一点。维特克并不否认自己一直在咳嗽,因为他患有花粉症和过敏性鼻炎,对灰尘很敏感。专家证实了维特克的证词,并且认为他的症状会因为摄影棚内干燥的空气而恶化。然而,控方律师轻蔑地指出:“没有理由让你在他说出正确答案时正好咳嗽,除非你刻意这样做。”
在伦敦萨瑟克刑事法庭审判的22天中,法庭上出现了非常多的咳嗽声。录影带中英格莱姆的表情被播放了很多次,而最关键的片段更是被重复播放,咳嗽声则被工程师放大。但咳嗽声不只来自录影带,一位坐在旁听席的记者注意到,每当律师提到“咳嗽”这个词时(当然,它出现得非常频繁),就会有旁听者开始咳嗽。当呼吸道疾病的首席专家提供证词时,一位女陪审员忽然咳嗽不止,庭审过程不得不暂时中止。在辩方律师结案陈词时,又有两名陪审员咳嗽发作,法官只得裁定休庭,直到他们不再咳嗽为止。
他们不是有意识地决定在得到这个提示时才咳嗽——这是下意识的、非自主性反应。如果指出他们的咳嗽和“咳嗽”这个词有关,他们一定会十分惊讶。先前节目的参赛者詹姆斯·普拉斯基特(James Plaskett)出版了一本关于英格莱姆审判的书籍,他全面分析审判的过程,认为维特克的咳嗽也许正出于和庭上那些犯咳嗽病的人同样的原因。一旦你同意人们咳嗽是因为外在的刺激,那么说维特克至少有几次咳嗽是出于对自己认为的正确答案的不自主反应,就似乎具有说服力了。而且,我们也并不清楚是否所有的咳嗽都是他发出的。普拉斯基特观看卡佩尔获胜的录像时,发现她在说出正确答案与按下答案确认钮之间,有观众发出清晰的、可听见的咳嗽声,分别出现在她回答2000英镑、4000英镑、8000英镑、64 000英镑、50万英镑以及100万英镑的问题时,也就是说,最后10次作答中有6次出现了咳嗽声——和英格莱姆比赛时出现的咳嗽次数一样。
不管是对普通观众而言,还是对其他参与者而言,这桩案件充满了神秘性。后来,塔兰特发表了他的看法:“伦敦警察厅和专司欺诈行为的缉查处从未找出真相。”一位警方人员曾亲口告诉《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我们无法找到每一片拼图”。当然,本书的重点不在于探讨判决书是否执行了正义,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相信英格莱姆有罪?
当某人在观众面前赢得100万英镑时,自然会引发人们讨论他诚实与否的问题。然而,英格莱姆常常自我否定的行为,让答案渐渐发展为否定。节目团队本能地认为,有些地方不太对劲。当然,他们的直觉就像那些被要求判断强奸案是否真的发生的警探一样,无法去芜存菁。英格莱姆这位犹疑不定、声音优雅的中产阶级军官有他自己的文化包袱。“不显眼的好人”是塔兰特对他的第一印象——就一般人对益智节目赢家的印象而言,这样的男人是无法赢得比赛的。
或许,真正说服10位陪审员、媒体以及英国大众“英格莱姆有罪”的原因,还是在于他面临麻烦时的行为表现:困窘、怪异、毫无自信、缺乏魅力。在摄影棚的灯光下,他似乎在颤抖、不安,常常口齿不清。换句话说,英格莱姆表现出了我们直觉中的骗子的所有特点。
……
后记 如何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实生活三原则
了解了谎言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后,我们不得不努力思考,什么叫作“诚实”?诚实并非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拥有的,而是我们必须努力追求的品德。
一、分享
了解了谎言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后,我们不得不努力思考,什么叫作“诚实”?诚实并非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拥有的,而是我们必须努力追求的品德。
康德曾说自己景仰的是“头上拥有灿烂星空,内心拥有崇高道德法则”的人;达尔文和他的后继者却将人类描述为拥有不稳定内在道德指标的动物。我们绝对是自私的,我们天生就会先考虑自己的骨肉和亲属,是当代哲学家彼得·莱尔顿(Peter Railton)所谓的“我执(us-ish)”型动物。我们也已经知道,我们会被一些有用的错觉包围。我们大脑存在的目的不是用来寻找真相,而是用来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真相的。人类学家罗宾·福克斯(Robin Fox)说:“大脑的任务不是告诉我们正确或客观的世界观,而是给我们有用的观点——一个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的观点。”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这个由骨骼和肌肉组合起来的肉体能够存活、繁衍;虽然寻找意义很重要,但这只是它的第二考量。所以,对别人说真话也不是首要目标。
这不是说康德所景仰的是错误的。我们都必须学会纠正性格中的扭曲的部分,并克服偏心和成见,努力接近真相。如何做到这些呢?靠通力合作。首先,我们必须发展说实话的社会形态:依靠正确的道德准则,让我们了解诚实的好处;其次,继承和发展对的社会性思维模式:伏尔泰、培根、拉瓦锡及富兰克林给我们留下了有逻辑的、严谨的科学思考;第三,我们发展可以彼此监督的社会环境:在法律、民主、自由等机制上的进步,使得我们宣称的每句实话,都会受到挑战。
但这些当然还不足以让我们对抗不诚实或腐败,而且这些做法也完全不能改变我们的天性。但也许我们可以听听考斯顿的观点:人类是有缺点的生物,但让我们保持诚实的是我们的社会义务,而非抽象的道德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努力发展民主社会机制的原因。诚实的环境需要我们去一起营造。
二、不要相信你觉得确定的事
在现代文化中,我们十分强调要“相信自己”。我们都被教导要跟从自己的心意,相信自己的直觉。但我们的直觉也会有误区。例如,提摩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的研究指出,我们甚至无法正确地预估自己的行为——而我们的朋友,甚至知情的陌生人,会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将采取什么行动。是的,我们有预知自己思想和动机的能力,但这反而会让我们得到过多的信息。既然见树不见林,我们会基于对自己性格的错误分析,而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些奇怪的预测。我们会高估自己节食或健身的成效,低估自己爱上不该爱的人的惯性。我们关注那些并不存在的动机和意图,却否认那些真正存在的原因和想法。
“对自己诚实”,但不要太相信自己。我们都有一种自然的倾向,越是对于我们竭诚相信的事物,就越可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神经科学家罗勃特·伯顿(Robert Burton)认为,我们有一种被大脑激化的自我欺骗的错觉——他称为“知晓的感觉”。当我们坚持己见,或是再次确认一个已经相信了很久的信念时,我们体验到的确定感是不可信的,它是我们设计出来的感觉;这种设计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决定(得以行动),但与决定的正确与否没有太大关系。
知晓的感觉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因为它鼓励我们拒绝或不要考虑反对意见,并容许一种不理性的偏见来主导我们的心灵(例如我们过度相信自己能够辨别他人是否在说谎)。我们必须自我防卫,不要上了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的当。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曾说过:“首要原则是不要愚弄自己,你是最容易上自己当的人。”
当然,活在100%的确定性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合理范围内,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我相信”来代替“我知道”,即使这代表我们其实并非那么全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评论道,多数人认为自己的信念有100%的正确性,但较合理的估计应该是60%左右的正确性。承认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现在就试试看,你会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我们少聆听一些自己的“知晓的感觉”,多听听别人的意见,这个世界应该会变得更美好。
三、为错觉保留存在的空间
在温哥华岛和北美太平洋的海岸之间,有一条狭长的水域,这里聚集着峡谷、茂密的森林、岩石群和几乎难以穿越的岛屿。几千年来,加拿大夸扣特尔(Kwakiutl)的渔民们居住在跟温哥华岛毗邻的大陆上。夸扣特尔人以制作精美的陶艺而闻名,他们有一种类似冬季赠礼节(potlatch,印第安人的节日)的特殊习俗,不同社群的首领会竞相放弃他们的财富。另外,他们也因为盛产巫师而闻名:通过与神祇沟通而治愈患者的治疗者。1887年,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这位人类学家记录下夸扣特尔巫师吟诵的治疗之歌,那位巫师的名字叫奇撒利德(Quesalid)。在录下他的声音后,鲍亚士也记录了许多年前奇撒利德成为巫师的过程。
年轻时的奇撒利德曾是个愤世嫉俗的家伙。当时,北美部落中的巫师是介于牧师、医生和摇滚明星之间的身份,他们被尊重甚至被敬畏;同时,他们的服务收取高昂的费用。在奇撒利德的家人和朋友眼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对巫师的财富和地位不满的人。他认为,巫师们欺骗了那些有需要的、脆弱的蠢货,所以他想了个办法来揭发他们的罪行。首先,他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才能够得知他们的秘密,然后他打算把这个秘密告诉全世界,以此消解他们的神圣。
他开始与当地的巫师接触,终于有一位巫师收他当学徒,而奇撒利德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欺骗:他被教导如何假装昏厥和神经痉挛(巫师必须表现出跟神灵奋战的样子),以及如何担任“做梦者”:巫师任用的间谍,会在村子里偷听村民的私密对话,并转达给巫师,所以巫师才能够表现出深谙患者病况的样子。
奇撒利德甚至了解到最大的秘密——夸扣特尔巫师重要行动的真相。当部落有村民生病时,会征询巫师的意见,如果巫师断定病况是值得治疗的,就会举行一场精心策划的仪式。仪式上充满了音乐、歌唱和吟诵,巫师会靠近病人,把他的嘴贴在病人的患处——例如患者的胸膛——做出像是吸取病人身体里的恶灵的样子。现在,奇撒利德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巫师在嘴里藏了一小片鹰毛,然后咬破自己的嘴唇。等到鼓点越来越快,音乐到达高潮时,他抬起头来,吐出被血液浸湿的羽毛。
奇撒利德的猜测得到了证实:巫师最厉害的神力不过是魔术手法和蹩脚的欺骗手段。他打算对大众公开他的发现。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奇撒利德被一户村民叫到家里去,说他家的孩子梦到奇撒利德将会成为他的治疗者。这是部落的惯例,当生病的人梦到治疗者时,那个人就是最可能治愈患者的巫师。面对这个绝望的请求,奇撒利德不忍拒绝。夜晚来临时,邻村的人驾着独木舟来接奇撒利德。已经藏了些鹰毛在嘴里的奇撒利德,准备进行他第一次的治疗仪式。
他一上岸就立刻被请到孩子的祖父家。屋子中间已经点起了火把,周围站满了前来围观的村民和儿童。生病的孩子就在屋子后面,他看起来非常衰弱,而且呼吸急促。奇撒利德跪在他身旁时,男孩睁开眼睛,指着他自己的肋骨下方低声说道:“欢迎你的到来,请发发慈悲救我一命。”奇撒利德的嘴巴靠近男童的身体,同时咬破自己的舌头。几秒之后,他抬起头来,在掌心吐出血渍。当他起身围着火把跳舞时,音乐变得更大声、更快速,他唱着圣歌,并将男童的“疾病”展现给大家看,然后把羽毛丢进了火炉。这时,男孩坐了起来,他已经恢复了一大半。
以下是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伯(Alfred Kroeber)在1952年的记载:
接下来的是一个关于欺骗的老问题。或许全世界大部分的巫师及治疗者都曾经用魔术手法治疗过患者,也曾经展现过“神的力量”,这种戏法有时候十分精细。在许多案例中,即便巫师知道自己行使诈欺手法,但仍旧相信这种力量,以及其他巫师的力量:他们自己或子女生病时,也会求助于其他巫师。
即便不情愿,奇撒利德也已经从学徒变身为巫师,从欺骗的敌对者变成错觉的共谋者。虽然这个故事发生在距离我们十分遥远的社会,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引发的问题却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的。
剧作家艾伦·班尼特(Alan Bennett)认为,“做自己”其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指令”。班尼特强调,或许它真正的意思是“假装做自己”。社会学家欧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指出,舞台和真实人生的界线模糊到让人惊讶。当然,要成为好演员需要技巧和训练,但这并不妨碍大部分人在有了剧本和简单的指导后,就能够以具有真实感的方式向观众传达情绪。高夫曼说,这是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充满戏剧性的”。一般的社会互动就是即兴演出,我们的“表演”已经足够生动。在高夫曼的观点中,我们都是忘了自己是在演戏的演员。大多数时候,我们既知道别人在对我们演戏,同时又相信这样的表演。在《便士巷》(Penny Lane)中,披头士吟唱了许多主角:银行家、消防员和理发师,他们都是街道的一景;一位年轻护士用托盘出售罂粟,让她觉得自己像是在演戏一样。“而她的确是在演戏。”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唱道。
在易卜生(Henrik Ibsen)的《野鸭子》(The Wild Duck)一书中,主角说道:剥夺一名男子的生活谎言,等于夺走了他的快乐。易卜生相信,我们许多人都知道现实并不愉悦,因此我们戴上了理想主义的面具(这个面具同时也是我们的挡箭牌),它为我们创造了另一种生活。这是在现代戏剧和文学,尤其是美国传统的戏剧和文学中最常见的主题,它和中产阶级苍凉无望的未来有关。想想看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推销员、约翰·契弗(John Cheever)的游泳者(约翰·契弗是美国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游泳者》描述了主角在游泳回家的过程中发生了超现实事件)、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美国作家)的主角常有的幻想与羞怯,以及在电影《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中有自我毁灭倾向的主角莱斯特·伯哈姆(Lester Burnham)。在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的《送冰的来了》(The Iceman Cometh)里,主角宣称“是白日梦的谎言给了我们这些可悲的疯子生命,不论酒醉或清醒”。在这些故事里,生活的谎言都被塑造成是“飞离真诚的欺诈号航班”,艺术家的工作则是揭开这个面具。
我们必须和现实紧密接触,同时又强烈需要去诉说一些不真实的故事,并且相信这些故事。没有前者,我们就无法跟环境共处或跟其他人共处;没有后者,我们将缺乏让人类进步的想象力。或许我们应该同时尊重这两种需求,泰然地戴上我们的面具,但是又不能忘记自己脸上有面具。用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话说,“相信小说,虽然你知道它是虚构的”。
在治愈了第一位患者后,奇撒利德被奉为伟大的巫师。几年下来,他因为做了原本不愿意做的虚假之事而成名致富。也许,唯一不相信奇撒利德能够演示这种神奇力量的人,就是他自己。但随之而来的成功已经动摇了他原本持有的怀疑,他表示,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万分骄傲。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