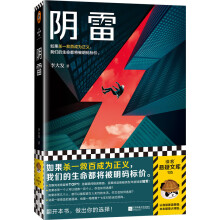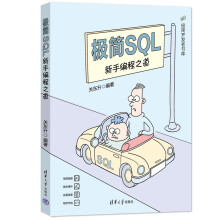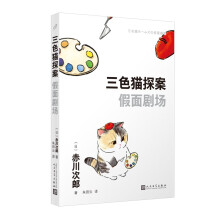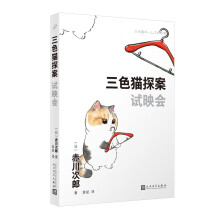文献记载也不乏其例,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载:“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一)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其中“建除”、“丛辰”均见睡简《日书》,“天一”见于马王堆帛书。可见武帝也是信用(日书)的。《漠书.王莽传上》:十一月“以戊辰日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以秦简《日书》建除术推之,十一月“建”子,“定日”值辰。可见王莽也是信用《日书》的。《后汉书。皇后纪上》:“十七年正月,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所谓“案历明旦日吉”之“历”,显然也是(日书)一类的择日书。所以,从《日书》使用者的社会阶层看,可能与卜筮祭祷简相似,也是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士庶百姓,其反映的宗教信仰,是较具普遍意义的。
目前发现的战国楚简帛文献中的方术材料,主要是卜筮和择日(选择)两大类,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史记》的《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太史公“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作《太史公书》,而与民间方术活动有关者,亦仅《龟策》与《日者》二传,这不能不使人怀疑,直到太史公司马迁之时,当时在民间基层社会活跃的方术,恐怕是以此二者——卜筮与择日——为主流的。吕思勉先生很敏锐地观察到了遣一点,他说:“《史记》有《日者》、《龟策》二传,则时日、卜筮,实为古人趋吉避凶之术之两大端,盖事有可豫测其吉凶而趋避之者,时日是也。有无从豫见,必待临事求其征兆;或征兆先见,从而占其吉凶者,龟筮、杂占是也。吉凶既可豫知,自可从事禳解,故《周官》占梦,有赠恶梦之法;而《汉志》杂占家,亦有执不祥,劾鬼物,请官除妖祥及禳、祀、请、梼诸书焉。”①其说甚为有见。《楚辞.离骚》云:“灵芬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