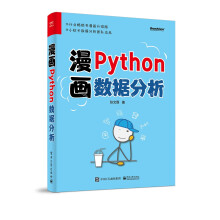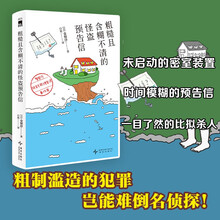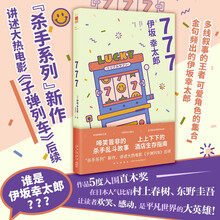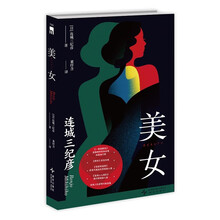晚清的孙诣让在《古籀余论》中,据《扩古录金文》摹本考释五年碉生簋铭(孙氏称此簋为“召伯虎敦第二器”,第一器为六年碉生簋)。他将“厦”释读为“妇”,以为“妇氏盖内官世妇之属”。②《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谓其说“近是”。③其它研究碉生簋的学者,大抵也都信从释“厦”为“妇”之说。至于“妇氏”的身份,则有林涹先生在《碉生簋新释》中提出了“妇氏”指召族的“宗妇”,“应即召伯虎之母幽姜’,的新说。”此后,绝大多数研究者接受了“妇氏”指宗妇的意见,只是对“妇氏”究竟指召伯虎之母还是召伯虎之配,则有歧见。
我们认为从文字学角度看,把“区”释读为“妇”是缺乏根据的。前面说遇,古文字中从“帚”与从“曼”有时可以相通。这并不是说,所有从“帚”之字都可以写成从“曼”。例如“归”字的“帚”旁,就不能换成“曼”(《金文编》第85页“归”字条所收貉子卣之字,右半作“曼”。此卣器盖同铭,见《集成》5409。其字形颇为整饬,只有“归”字右旁“帚”的下端多出很小的似笔画非笔画的痕迹,似是作字模时去掉写错的笔画后留下的残痕,《金文编》的摹录是不忠实的,对照原铭可以清楚看出)。“妇”字也是如此。古文字中的“妇”字从来没有写作“熳”的。殷墟卜辞极少用“妇”字,一般借“帚”为“妇”,“曼”则从来不借为“妇”。所以“产”虽有作“寤”的异体,仍不应释读为“妇”。释读为“妇”,对此字所从的“山”也很难作出交代。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