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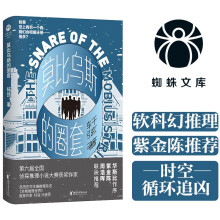




他甚至为清廷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行径辩护,说朝廷“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已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劝学篇·内篇·教忠第二》)。《劝学篇》虽有“劝工、劝农、劝商”之倡,但限制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轨范之内。张之洞说:“华商陋习,常有藉招股欺骗之事;若无官权为之惩罚,则公司资本无一存者矣。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为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只有在官权的保护之下才能实现。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却证明,正是强势官权阻碍了工业化的步伐。可见,张之洞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所开的处方,限定在官僚政治的体制之内。
《劝学篇》外篇关于学习西政、西艺的主张,包含着不少开明意见,它们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派学习并推行西方技艺、军事、教育等近代事业的全面概括,而且把“西学”的范域从技艺层面推及到文教制度层面,并涉人政治制度的浅层。
《劝学篇》刊行的时机,也活生生地昭示了这部著作特有的政治色彩。
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变法运动进入关键时刻。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以后,决定变法;接着又召见梁启超,后又特授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专办新政。与此同时,慈禧也采取对策,在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后四天(6月20日),即迫令光绪帝将翁同觫开缺回籍。“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毹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①慈禧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掌握近畿兵权,随时准备朝维新派猛扑过去。光绪帝此刻的处境是,既想变法维新,又“上制于西后,下壅于顽臣”,无所措手足。正在这一微妙时刻,张之洞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以张之洞所著《劝学篇》进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