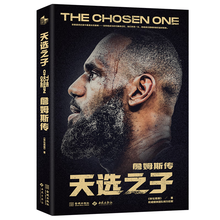我这些年曾给父母寄回了许多外汇,母亲把我看成一个有钱的美国公民而估算我的权势,她觉得十分惬意。我现在了解到,这些外汇的大部分都上交了国家,①因为他们住在远离海岸线一千英里的小城市里,而这里的日用品供应很缺,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高档商品更是无货。她曾写信给我说:“给我带回单子上所列的物品。我们街道领导曾替我打听过,据说,这些物品将要在广州过关,有些上税100%的物品可以减免一部分。”她听到的消息是确实的。
这样评价我的母亲,也不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自从一九四九年我飞抵美国以来,父母直接寄给我的第一封信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才收到的;信是父亲写的,不过,就像母亲写的一样,而且带有她的尖酸刻薄味儿。我收到这封信是在五月三日的早晨,这一天正是我丈夫②最新的一条船在德克萨斯州的奥兰治城命名和下水的日子。我们邀请了上千名客人参加盛会,我想谁也不会注意到在这个本应当是欢乐的日子里我所感到的痛苦。从小我就学会了如何掩盖自己的感情,那一天的早上和下午,我本似乎应该被这一盛典吸引住,但是我却只想单独一个人一遍又一遍地看这封来信。我感到了已被长期忘掉了的创伤的苦痛。我明白自己又落入母亲的权力掌握之中了。
三十多年来,我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我寄钱回去并请求来信以及我写信告诉她我生了三个孩子之后,也都没有收到来信。同时,父亲也没有来信,我怀疑,母亲一直在选择某一合适的时候才许可父亲写信。是我的大姐艾丽丝(小惠)来信告诉我家里人的健康情况,也使我知道寄去的钱已收到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写过七封信,在政治解冻以后,也写过七封信——有礼貌的短信,却充满着无声的感情。这回父亲写来的短信,笔体仍然秀丽;但这仅只两页的信,却像重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口袋里。信中的请求并不通情达理,简直是毫不客气。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