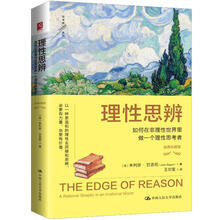1995年,我国出现“顾准热”的时候,我正身处异国他乡。回国以后,陆续收到三本有关顾准的著作:《顾准文集》、《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我如获至宝,反复研读。如饮甘露,似嚼橄榄,受启发良多,余味无穷。对顾准的认识比过去全面、系统、准确、深化多了。当此纪念顾准九十诞辰之际,作为顾准多年的同事兼学生的我,也来步学术界的后尘,对他作些追思,以期集思广益,交流切磋。
不具慧眼,难识真佛。要说跟顾准的接触与交往,笔者比一般局外人士要多得多。我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息县干校与他共处多年,而且还于1966年将近一年的期间里,在房山县大韩继村建筑工地上与他一道被监督劳动过。其实我们经常交流思想、谈古论今。偶尔也开开玩笑,苦中作乐一番。是年,他51岁,我30岁,可称得上“忘年交”。他是性情中人,口无遮拦、爱发议论、锋芒毕露、喜怒常形于色,生气时也会骂娘。与这样的人相处,不累,还挺有意思。说实在的,当年虽说我很佩服他:会计专家、英语精通、学贯中西、敢讲真话等等,但没有达到眼下学术界对他评价的高度;卓越的思想家、预言家、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者与理论先驱等等。综观顾准的方方面面,以上评价恰如其分,绝无溢美之嫌。大凡要较全面准确地认清与评价历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往往需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或甚至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兴许是一条客观规律吧。正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
当年,他是“极右分子”,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时,我还不到而立之年,怎么就摊上了这么可怕的罪名?说起来是“水土不服”,时机不巧所至。
我在1960年秋,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分配在经济所工作。1961年夏,被下放到河北省昌黎县人委财委从事协助管理集市贸易的工作。农村集市自1961年初开放以后,对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好的作用。到了1962年4、5月份,传来关于集市要重新关闭的小道消息。我写了一篇《昌黎农村集市贸易调查报告》,寄回所里。里头讲了一些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是修正主义,至少是“右倾”的观点,诸如:农村自由市场利多弊少,不可时开、时关;对集市应“统其大纲、无为而治”;长途贩运不应算违法,只要对生产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农业生产应以经济杠杆为主,思想教育为辅;农村一次次整风不能解决干部民主作风问题,关键是规章制度,不可一个人说了算,应搞包产到户作权宜之计等等。9月份,所长孙冶方给我回了封亲笔信,说《调查报告》很好,已在中央内部刊物《财经通讯》发表,受到首都各界重视,请继续调研,及时上报,供中央决策参考云云。我有些小虚荣心,将此信给不少人看过。到了1964年10月,康生派了一个庞大工作组到经济所搞“四清”。当工作组向我要孙冶方的这封信时,我把它烧掉了。我刚回国不久,实在不知道政治运动中“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新道德标准,还自认为这是古之“君子”、国际上之“汉子”的行为。这是“水土不服”所至。为什么说“时机不巧”呢?后来得知,1961年1月份召开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作了些检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把陈云请出来主持恢复经济的工作,推行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经济很快有所好转。这期间,彭德怀提出“本反”的申诉,又出了小说“刘志丹事件”。毛泽东开始反击,在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以及9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正在这节骨眼上,孙冶方说我的《报告》受到首都各界重视,要我继续上报。这不是蓄意地组织人马与毛泽东唱对台戏吗?我将这么重要的“罪证”付之一炬,很可能惹怒了“四清”工作组、上面的牵线人康生之流。于是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运动中烧毁重要罪证”。这样,我日后就经常需要与顾准这类“分子”为伍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