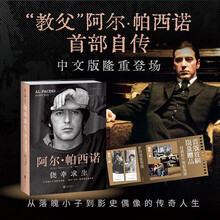故乡桑植
我们(即作者同何其芳及鲁艺同学)由湘鄂边境的战事谈到长沙大火和他(即贺龙同志,下同)的故乡桑植。
“据说,桑植就是从前的夜郎国,——所谓夜郎自大呀。”
他半眯着眼睛,意味深长地笑了。
“人民强悍得很!”他接着说,态度变得认真起来,“从前老喜欢械斗,打死个把人不算回事。马江口一家姓顾的,为一点小事,叔父把侄儿杀死了;侄儿的两个儿子赶场,在路上拦住这个叔公,又把他杀了,连手连足都砍了,头也砍了。都才这样高的人呢!”
他比着高矮,在一种苦恼的兴奋里沉默下来。
“同志!”他随又叹息道,“这就是野蛮呀!”
我们请他告诉我们械斗最普遍的原因。
“这多啊,”他伸出手,扳着手指头讲起来了,“为世仇,为正月里赛灯,为水,为界址,经常都是引起械斗的导火线!一闹大了,总是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经常打得头破血流,就是把皇帝老子搬出来都挡不住!”
“可以举几个实例吗?”
何其芳追问着,但他似乎没有听见。因为他的脸上依旧兴奋而又苦恼,眼光聚拢着,紧闭着嘴,好像他又重新看见了那种大胆粗豪的风习,或者如他所说的野蛮的生活场面了。
“不过野蛮虽是野蛮,”他忽又显得满意地注视着我们,声调柔和起来,“也有他们的长处呢:朴质,好胜,有骨气!不管是拿官、拿钱都买不到他。并且很勇敢——单跟着我就牺牲了不少的人。”
他骄傲地,然而略带忧郁地笑了。
他从裤袋里摸出烟包,装上烟吸起来。这一些都照例做得那么从容,那么有条不紊。而且,在装好烟后,照例十分巧妙地把烟斗送进卷起的手指间,几转,去掉那些尘埃一般的烟末。
这中间,我问起桑植从前贫富之间的关系。他笑答道:“阶级关系相当尖锐。就拿放利说吧,有大加一,跟斗翻,我自己家里就是被剥削的。小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借钱付利不算,还要说好话,送人情。可是,穷人也并不弱呢!一到年成饥荒,总是一个吆喝,就把地主的谷子分了。”
父亲
“一年天旱,农村里吃大户,闹得轰轰烈烈。眼看城镇上的老百姓也动起来了,公家就借了一批谷子粜米。因为我父亲是缝工(即做衣服的裁缝),一边种一点儿地,家里糊不圆了,也跑进城去籴米。带着我同他一道,担了这么大一对箩筐,你想,这装得到多少呢!
“粜米的地方在大堂边,那好多的人啊!你挤我,我挤你的,都想早一点把米搞回去下锅。可是那些狗腿子偏不肯发,要等杜老爷来了再说。杜老爷是房里的老典,很有势力,他是主办这一件事情的。这有什么办法昵,大家只好等下去了。
“可是杜老爷不来,而籴米的人愈来愈多,都在往前面挤。这把那些差人惹毛了,拿起皮鞭就打!……
“我父亲拳术很好,可以打十几个人,就去讲公道话。
“大家是来籴米的,不是来挨皮鞭的,怎么要乱打呢!?’
“话才说完,那些狗腿子就给他一鞭子;他一闪,鞭子恰恰打在我手上,这一下把我父亲惹毛了!……
“我父亲立刻把我抱起,挤出去,搁在人堆外面一个高坎上面,说,你把箩筐看好!就又跑转去了,把鞭子夺过来,给他好一阵乱打。随后杜老爷跑出来,又叫他一顿打起。那真搞得痛快呢!可是结果开来一批堂勇,把我父亲抓去关起来了。
“好在我们两个堂叔出力,才关了一夜就放出来了……”
姐姐贺英
我向他提起他的大姐贺英(亦叫贺民英)同志。他第一次向我提到这个杰出的女性是在延安。她是他初次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合作者,而在以后,每次遭到失败,她都帮助他重新成立起队伍。她是在1934年[应为1933年]的湘西游击战争中牺牲的。
“她并不懂得理论,”握着烟斗,他曾经背靠在延安一所平房的柱子上给我说道,“但是她的理解力很强。胆大,天分比我们高多了。她说队伍要‘武’,就是说要打仗,‘不武’就要坍台!”
他得意地微笑了。……
但使我发问的,是他在抗大女生队成立时的一场讲演。在这场讲演中他曾经谈到贺英同志,后来听讲者之一——我爱人黄玉颀,把她自己的感奋和当时的情形全部告诉我了,所以我就从这点说起。
“听说毛主席那天也很兴奋呢。”我加上说。
“好像有这回事。”他含糊地回答说,接着却又认真地说了下去,“她确实很能干,不管多少队伍,她都能够统制。她知道怎样使用干部。许多土匪头子都怕她,那些人正像大山里赶下来的猴子,调皮得很。我第一次成立红军的队伍,就是她分给我的。”
他顺下眼睛,陷入了深思,一面静静地吸着烟斗。
“就拿给养问题说吧,”一分钟后,他又不大自然地继续说道,“哪里像这样,半天还弄不到吃的!她总是自己骑匹骡子赶在前面,队伍一到,什么饭呀、水呀通弄齐了。”
19岁,搞湘西暴动
“我才10岁就一个人到四川涪陵做生意,一来一去千多里路,沿途都是土匪。还到过贵州做马生意,总是百十匹的买;放到辰州去卖。一直把赚的钱玩光了才回家!……”
大约忽然想起了年轻时候他所接触过的旧社会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早已同他水火不相容了,他忍不住笑起来。
“就是1915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时候我的岁数也并不大呀,”他接着说,“才19岁!同盟会要我搞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就找些人把石门县的团防局的枪提了。转来碰见我的叔父,我说,斋公!我们去提盐运局的枪好吧?于是气都没歇,我们又掉转头搞盐运局去了。这一来我们就去进攻大庸,人数也增加了。”
“你们还没有看见农民轰动起来的时候那个隋形啊!简直挡都挡不住!凡是和我认识的年轻人,都参加了。都是一律打扮,挖了云子的白绸短打,黑纱套头——后面拖这么长!不过因为城里住着一旅北洋兵,打死我们好几百人,第三天上,剩下来的几乎全跑光了。”
“这都是小事,”他愤愤地继续说,“最坏的是那班势利鬼。你刚搞对了的时候,他捧你,说,这些茅荆条了不得,说干就干!你一失败,他就把嘴一撇:这些人都搞得出事来吗?我早就说过吧!”
他闷着脸停歇下来,仿佛他正面对着那种渺小庸俗的市侩一样。而那位年轻秘书于是带点挂虑问道:
“后来又怎样呢?”
“后来我把剩下来的队伍拖到辰州,跟着就下野了……”
沉默一会儿,他接着又说:“虽说是下了野,被摘了兵权,因为一个民军领袖的地位依然存在,所以当时新上台的督军谭延闽,不但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仇敌,还委为督军署的咨议,并且拨出进口的两只粮船让我收税;但我跑到长沙去了。”
“我记得是坐的戴生昌的船,”他回忆着说,“路上打了账房一顿,就东西也不要,跳上岸走了!但是到了长沙,更加闹得厉害,酒馆、戏院,没一处没有我,简直一塌糊涂!”
他纵声大笑起来,之后,却又用一种哲学家的口气说:“不过,胡闹是胡闹,同志!长沙这两年的生活,对我的影响也蛮大呢。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
和县衙的领班打官司
“你们不要看,”次日下午,他又来同我们谈起他的幼年,“我小时候还打过官司呢!”
“大家都晓得的,清朝时候一个领班那多凶啊!什么案件都要先经过他,手下总是养起好几十个徒弟。我们县里的领班叫陈小涛,无恶不作,随便提人呀,勒索呀,什么坏事都干。他的两个儿子更是豪强霸道,没有人惹得起。一骑起马来那个劲呀,不管人哟,摊子哟,撞翻了你自己倒霉!
“有一次,他跑到我们那里去了,照例骑起马在街上乱撞,我就拖出一根棍子,站在大门口说:‘是好样的你给老子来撞!’
“这个狗娘养的硬是撞来了呢!我就给他一顿打起。许多哥兄弟呀,也都出来帮我。因为满街全是我们姓贺的。还不到半点钟,就打得他头破血淋,赶紧跑了。这一下大家好开心呀!
“可是,一跑回去,马上就在衙门里告了我,大家就又替我担心起来了,说,这下怎么办呢?我父亲也有点着急。到了审问那天,把我们族里的好多有功名的人都请来了,预先教了我怎样做口供,免得取不脱手。因为实际上是我打了别人呀!
“你们没有看过清朝时候问案的情形,好威风哟!你一跪下去,就夹棍、板子,啪地一声堆在你面前。……
“说起来我也蛮胆大呢,我才不管你那一套!我说‘我怎么敢打他呢!我在街上买东西,他们骑起马乱撞,把我的酒罐呀,油罐呀,全碰烂了,要他们赔,还打我一顿!……’
“除了这个,我另外还有个供词,是一个姓王的举人教给我的。这个举人和陈小涛不对得很——这也是个无恶不作的恶棍,后来叫老百姓杀了。他要我暴露陈小涛的黑幕:怎样勒索人,挖苦人,见钱就想。并且要我咬定那个小领班是下乡抓人的。所以,结果连陈小涛的领班也革职了。”
“这样说,你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讨厌官府了?”
“很小我就讨厌官府了!记得1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镇上来了一个禁烟委员,有喝道的,堂勇哟,一大串!这种情形在小孩子的眼睛里多好玩呀,我就跑拢去看。可是,还没有走近身,就一阵吆喝,把我赶起走了!连街沿都不准下。”
P12-18
……
展开